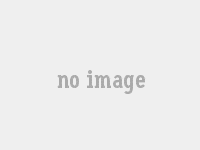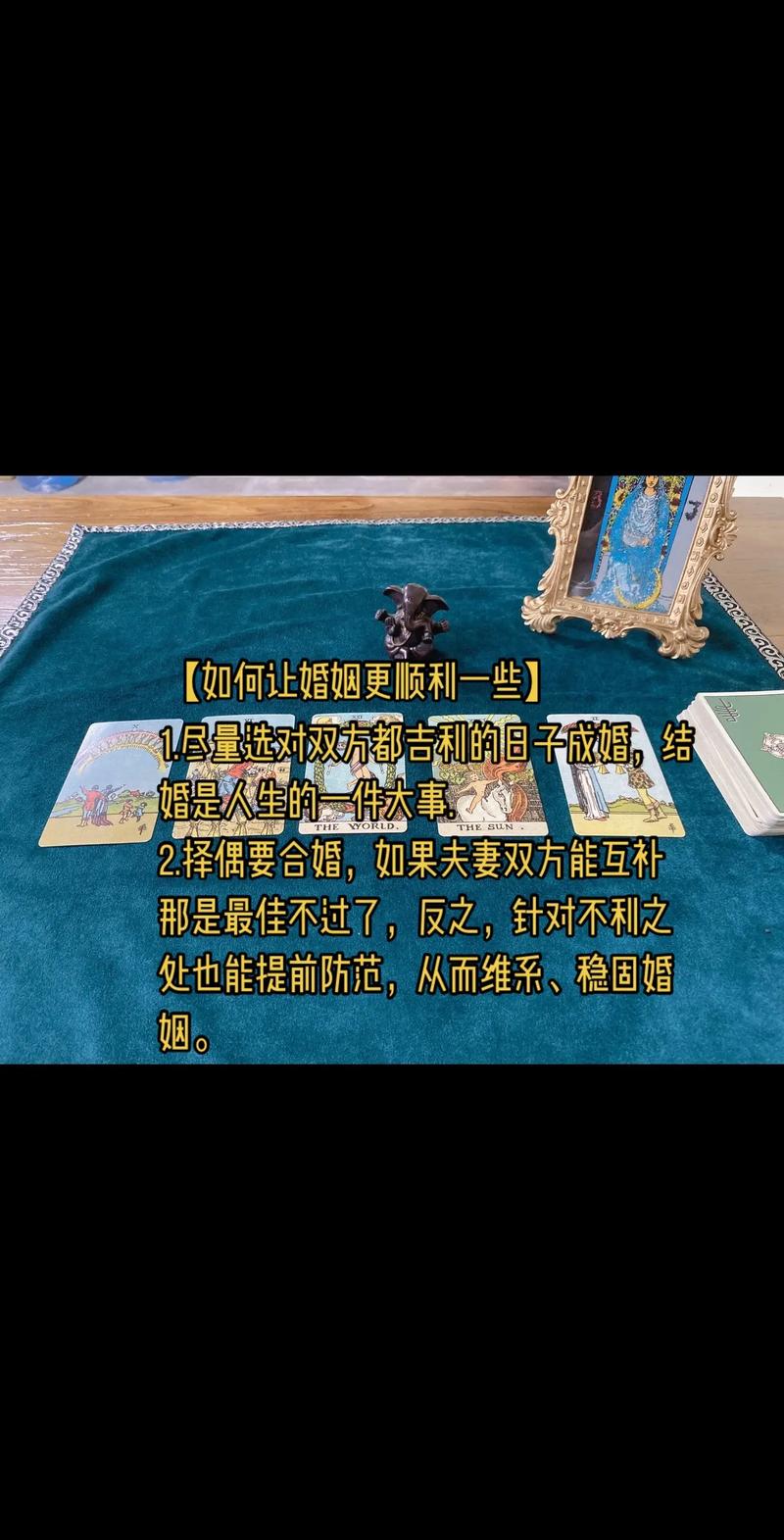一本好书:李娟《遥远的向日葵地》
我还有一个梦,就是过真正与大地相关的生活。这个梦里,我有一块土地,有一座结实的房子。
说起来,好像和我妈眼下这种日子没什么不同……
其实还是不同的。至少它更稳定,更长久,更简单。
这个梦对我来说时远时近。有好几次,我都已经下定决心。我开始在我妈所在的村子里寻找合适的宅基地,开始画设计图纸。
后来我去了城市,仍念念不忘这个计划。每当我为生活杂事奔忙,焦虑疲惫,难以入睡,我便闭上眼,抱着枕头,在黑暗中继续展开庞大的计划。我不停改变设想,纠结于无数细节……直到满意地沉入睡眠。
我去过很多地方,住过好多房子,睡过各种床。我想,这一切都是暂时的。所以,我从不曾畏惧过生活的改变与动荡。
后来我和外婆一同生活,养了小狗赛虎,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与收入。忙忙碌碌,安安静静。那时,我的大地上的房子仍马不停蹄地在心中营建,一砖一瓦反复修改。
我总是不得安宁,心中焦虑嘈乱。总是安慰自己:暂时的罢了,等有了房子就好了。
可我知道,我正在离那座院子越来越远。
乌伦古河从东往西流,横亘阿尔泰山南麓广阔的戈壁荒漠,沿途拖拽出漫漫荒野中最浓烈的一抹绿痕。
大地上所有的耕地都紧紧傍依在这条河的两岸,所有道路也紧贴河岸蔓延,所有村庄更是一步都不敢远离。如铁屑紧紧吸附于磁石,如寒夜中的人们傍依唯一的火堆。
什么都离不开水。这条唯一的河,被两岸的村庄和耕地源源不断地吮吸,等流经我家所在的阿克哈拉小村,就已经很浅窄了。若是头一年遇上降雪量少的暖冬,更是几近断流。
因为在北疆,所有的河流全靠积雪融汇。
我常常想,一百多年前,最早决定定居此处的那些农人,一定再无路可走了。
他们一路向北,在茫茫沙漠中没日没夜地跋涉。后来走上一处高地,突然看到前方视野尽头陷落大地的绿色河谷,顿时倒落在地,痛哭出声。
他们随身带着种子,那是漫长的流浪中唯一不曾放弃的事物。
他们以羊肠灌水,制成简陋的水平仪勘测地势,垦荒,开渠。
在第一个春天的灌溉期,他们日夜守在渠边。每当水流不畅,就用铁锨把堵塞在水阀口的鱼群铲开。
那时,鱼还不知河流已经被打开缺口。更不知何为农田。它们肥大、笨拙,无忧无虑。
它们争先恐后涌入水渠,然后纷纷搁浅在秧苗初生的土地上。
秧苗单薄,天地寂静。阳光下,枯萎的鱼尸银光闪闪,像是这片大地上唯一的繁盛。
冬天,河面冰封。人们凿开冰窟,将长长的红绳垂放水中。虽然无饵无钩,仍很快有鱼咬着绳子被拖出水面。
这些鱼长有细碎锋利的牙齿。即使已被捉在手,仍紧咬红绳不肯松口。
它们愤怒却迷惑。世界改变了。
春天,鱼群逆流产卵。鱼苗蓬勃,河流拐弯处的浅水里,如堆满了珠宝,璀璨耀眼。若在此处取水,一桶水里有半桶都是细碎小鱼。
人们大量捕捞小鱼,晾干,喂养牲畜。牲畜吃得浑身鱼腥气。冬天,牲畜被宰杀炖熟后,肉汤都是腥的。世界改变了。
鱼越来越少,人越来越多。耕地不断扩张,沿着唯一的河流两岸上下漫延。
才开始它们如吸吮乳汁般吸吮河流,到后来如吸吮鲜血般吸吮河流。
再后来,河流被截断,强行引往荒野深处。在那里,新开垦的土地一望无垠。
无论在种子播下之后,还是农作物丰收之时,那片土地看上去总是空旷而荒凉。
而失去水源的下游湖泊迅速萎缩,短短几年便由淡水湖变成咸水湖。
从此,再也没有鱼了。
又过去了很多很多年,我们一家才来到这里。我们面对的又是一片逾万亩的新垦土地。
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路也是新的,荒野中两行平行的轮胎辙印。水渠也是新的,水泥坚硬,渠边寸草不生。仿佛一切刚刚开始。
只有那条河旧了,老了,远在数公里之外。河床开阔,水流窄浅。
而鱼又回来了。它们历经漫长而孤独的周折。它们彼此间一条远离一条,深深隐蔽在水底阴影处。
这块土地也许并不适合种植这种作物,它过于贫瘠。而向日葵油性大,太损耗地力。
但是,与其他寥寥几种能存活此处的作物相比,向日葵的收益最大。
如此看来,我们和一百年前第一个来此处开荒定居的人其实没什么不同。仿佛除了掠夺,什么也顾不上了。
和这块土地上的其他种植户一样,我们也在自己承包的地上种满了向日葵。
这一年,正是罕有的旱年。去年冬天的降雪量据说还不到正常年份的三分之一。
正是这一年,我妈独自在乌伦古河南岸的广阔高地上种了九十亩葵花地。
这是她种葵花的第二年。
葵花苗刚长出十公分高,就惨遭鹅喉羚的袭击。几乎一夜之间,九十亩地给啃得干干净净。
虽说远远近近有万余亩的葵花地都被鹅喉羚糟蹋了,但谁也没有我妈损失严重。
我妈无奈,只好买来种子补种了一遍。
天气暖和,又刚下过雨,土壤墒情不错,第二茬青苗很快出头。
然而地皮刚刚泛绿时,一夜之间,又被啃光了。
她咬牙又补种了第三遍。
没多久,第三茬种子重复了前两茬的命运。
总之,这是令人沮丧的一年。
尽管如此,我妈还是播下了第四遍种子。
所谓“希望”,就是付出努力有可能比完全放弃强一点点。
随着葵花一天天抽枝发叶,渐渐旺壮,我们的蒙古包便在绿色的海洋中随波荡漾。
直到葵花长得越发浓茂喧嚣,花盘金光四射,我们的蒙古包才深深沉入海底。
其实我家第一年种地时,住的也是地窝子。我妈嫌不方便,今年便斥巨资两千块钱买了这顶蒙古包。
唉,我家地种得最少,灾情最惨,日子还过得最体面。
第一年,我妈在南部荒野中种葵花,我在北边牧场上生活。之间遥隔两百公里。
我给我妈打电话,总是很难打通。要么她那边没信号要么我这边没信号。等两边都有信号的时候,要么她手机没电了要么我手机没电了。
好容易打通一次,却往往无话可说。
我们陷入沉默,各自抬头看天。彼此的呼吸迫在耳畔,两百公里的距离让我们深刻感受着彼此间的陌生。
五月初,一场沙尘暴席卷阿勒泰大地。我所在的前山丘陵地带也受到很大波及,不由忧心南面葵花地里的家人。
“老子!现在!正,站在一个,最高的地方。走了好远,好远,才找到,这么高的地方!”电话那头她一字一顿,竭声大喊,与风声抗衡。
我打断:“前两天沙尘暴,你们那边没事吧?”
那边精神一振,声音立刻又高了三分:“对了!老子打电话就是想说这件事的!操他先人!老子走了这么远,就想说这个。好容易才找到有信号的地方!找了两天!前天一直往东面走,昨天又往西走。今天仔细一想:不对!应该往北。北面虽然全是耕地,但正冲着河谷,对面就是永红公社……”
我再次打断:“沙尘暴,说沙尘暴!”
我手机快要没电了。
“对!沙尘暴!”那边又一次来了精神:“哎哟!吓死老子了!你不知道哟,天边,远远地,就像一堵黄土墙横推了过来,两边都看不到头!几层楼那么高!老子当时想:完了,这下全完了。老子全家都要给埋到地下了!老子这辈子都没这么害怕过呢!操他先人……”
风声忽剧,接下来的话忽闪闪听不清。
十几秒后,信号稳定了,她的叫吼声重新传来:“……葵花苗刚刚冒出头。我想:完了!这下苗子全给卷走了。就算不给风卷走,也要给土埋了!昏天暗地,跟天黑了一样!我们用毡子把地窝子的门洞塞得紧紧的,还是被漫进来的土气呛得咳嗽个不停。到处都是土,操他先人!——”
很快,信号稳定下来,通话恢复正常。她继续说:“……哎哟!你可没见那天的情形哟!吓死老子了,操他先人……”
“先别骂了!说后来的事,后来怎样了?”
“后来嘛,哎哟!你猜后来怎么着?苗都好好的!”
“我问的是人!”
“嘟——”电话断了。电量耗尽。
电话那头那个总是被不停抛弃的母亲后来怎样了?——电话一挂断,她就被掷向深渊。她顶着大风,站在大地腹心,站在旷野中唯一的高处,方圆百里唯一微微隆起的一点,唯一能接收到手机信号的小土堆上,继续嘶声大喊。
那时,沙尘暴已在几天前结束,恐惧早已消散。可她心中仍激动难息。
她无人诉说。每天一闲下来,就走很远的路,寻找有手机信号的地方。
这一天终于找到了,电话也打通了。
可是,几乎什么也没能说出。
当初决定种地时,想到此处离我们村还有一百多公里,来回不便,又不放心托人照管,我妈便把整个家都搬进了荒野中。
包括鸡和兔子,包括丑丑和赛虎。
想到地边就是水渠,出发时她还特意添置了十只鸭子两只鹅。
结果失算了,那条渠八百年才通一次水。
于是我们的鸭子和鹅整个夏天灰头土脸,毫无尊严。
她在葵花地边的空地上支起了蒙古包。丑丑睡帐外,赛虎睡帐内。
一有动静,丑丑在外面狂吠震吓,赛虎在室内凶猛助威。那阵势,好像我家养了二十条狗。
若真有异常状况,丑丑对直冲上去拼命,赛虎躲在门后继续呐喊助威。直到丑丑摆平了状况,它才跑出去恶狠狠地看一眼。
所谓“状况”,一是发现了鹅喉羚,二是突然有人造访。
我觉得鸡认路才不靠什么标志,也不靠记性。人家靠的是灵感。
我从没见哪只鸡回家之前先东张西望一番。
鸭子们要么一起回家,要么一起走丢。整天大惊小怪的,走到哪儿嚷嚷到哪儿。你呼我应,声势浩大。
黄昏时分,大家差不多都回家了。我妈结束了地里的活,开始忙家里的活。
她端起鸡食盆走出蒙古包,鸡们欢呼着哄抢上前,在她脚下挤作一团。
她放稳了鸡食盆,扣上沉重的锥形铁条罩(鲁迅提过的“狗气煞”,我管它叫“赛虎气煞”),一边自言自语:“养鸡干什么?哼,老子不干什么,老子就图个看着高兴!”
于是鸡们便努力下蛋,以报不杀之恩。
蛋煮熟了给狗们打牙祭。狗们干起保安工作来更加尽职尽责。
我做好了饭,在蒙古包里等我妈回家。等着等着就睡着了。
哪怕睡着了,也能清晰感觉到置身睡眠中的自己是何等微弱渺小。
睡眠是地球上第二巨大的事物。第一巨大的是安静。
平时种植户之间都客客气气,还能做到互助互利。可一到灌溉时节,一个个争水争得快要操起铁锨拼命。
轮到我家用水时常常已经到了半夜。我妈整夜不敢睡觉,不时出门查看,提防水被下游截走。后来她干脆在水渠的闸门边铺了被褥露天过夜。
尽管如此,我家承包的两百亩地还是给旱死了几十亩。
接下来又病虫害不断,那片万亩葵花地无一幸免。田间地头堆满花花绿绿的农药瓶。
我妈日夜忧心。她面对的不但是财产的损失,更是生命的消逝。
亲眼看着一点点长成的生命,再亲眼看着它们一点点枯萎,是耕种者千百年来共有的痛苦。
直到八月,熬过病害和干旱的最后几十亩葵花顺利开完花,她才稍稍松口气。
而那时,这片万亩土地上的几十家种植户几乎全都放弃,撤得只剩包括我家在内的两三户人家。
河下游另一块耕地上,有个承包了三千多亩地的老板直接自杀。据说赔进去上百万。
冬天我才回家。我问我妈赔了多少钱。
她说:“操他先人,幸亏咱家穷。种得少也赔得少。最后打下来的那点葵花好歹留够了种子,明年老子接着种!老子就不信,哪能年年都这么倒霉?”

外婆倒是很高兴。她说:“花开的时候真好看!金光光,亮堂堂。娟啊,你没看到真是可惜!”
整个冬天,小小的村庄阿克哈拉洁白而寂静。我心里惦记着红色与金色,独自出门向北,朝河谷走去。
大雪铺满河面,鸦群迎面飞起。牛群列队通过狭窄的雪中小路,去向河面冒着白气的冰窟饮水。
我妈锁了门,发动摩托车,回头安排工作:“赛虎看家。丑丑看地。鸡好好下蛋。”然后绝尘而去。
被关了禁闭的赛虎把狗嘴挤出门缝,冲她的背影愤怒大喊。
丑丑兴奋莫名,追着摩托又扑又跳、哼哼叽叽,跟在后面足足跑了一公里才被我妈骂回去。
我妈此去是为了打水。
地边的水渠只在灌溉的日子里才通几天水,平时用水只能去几公里外的排碱渠打水。
那么远的路。幸亏有摩托车这个好东西。
她每天早上骑车过去打一次水,每次装满两只二十公升的塑料壶。
我说:“那得烧多少汽油啊?好贵的水。”
我妈细细算了一笔账:“不贵,比矿泉水便宜多了。”
排碱渠的水能和矿泉水比吗?又咸又苦。然而总比没水好。
这么珍贵的水,主要用来做饭和洗碗,洗过碗的水给鸡鸭拌食,剩下的供一大家子日常饮用。再有余水的话我妈就洗洗脸。
脏衣服攒着,到了水渠通水的日子,既是大喜的日子也是大洗的日子。
其实能有多少脏衣服呢?我妈平时……很少穿衣服。
她对我说:“天气又干又热,稍微干点活就一身汗。比方锄草吧,锄一块地就脱一件衣服,等锄到地中间,就全脱没了……好在天气一热,葵花也长起来了,穿没穿衣服,谁也看球不到。”
我大惊:“万一撞见人……”
她:“野地里哪来的人?种地的各家干各家的活,没事谁也不瞎串门。如果真来个人,离老远,赛虎丑丑就叫起来了。”
于是整个夏天,她赤身扛锨穿行在葵花地里,晒得一身黢黑,和万物模糊了界线。
叶隙间阳光跳跃,脚下泥土暗涌。她走在葵花林里,如跋涉大水之中,努力令自己不要漂浮起来。
大地最雄浑的力量不是地震,而是万物的生长啊……
她没有衣服,无所遮蔽也无所依傍。快要迷路一般眩晕。目之所及,枝梢的手心便冲她张开,献上珍宝,捧出花蕾。
她停下等待。花蕾却迟迟不绽。赴约前的女子在深深闺房换了一身又一身衣服,迟迟下不了最后的决定。我妈却赤身相迎,肝胆相照。她终日锄草、间苗、打杈、喷药,无比耐心。
浇地的日子最漫长。地头闸门一开,水哗然而下,顺着地面的横渠如多米诺骨牌般一道紧挨着一道淌进纵向排列的狭长埂沟。
渐渐地,水流速度越来越慢。我妈跟随水流缓缓前行,凝滞处挖一锨,跑水的缺口补块泥土,并将吃饱水的埂沟一一封堵。
那么广阔的土地,那么细长的水脉。她几乎陪伴了每一株葵花的充分吮饮。
地底深处的庞大根系吮吸得滋滋有声,地面之上愈发沉静。
她抬头四望。天地间空空荡荡,连一丝微风都没有,连一件衣服都没有。
世上只剩下植物,植物只剩下路。所有路畅通无阻,所有门大打而开。
水在光明之处艰难跋涉,在黑暗之处一路绿灯地奔赴顶点。——那是水在这片大地上所能达到的最高的高度。一株葵花的高度。
这块葵花地是这些水走遍地球后的最后一站。
整整三天三夜,整面葵花地都均匀浸透了,整个世界都饱和了。
很久很久以后,当她给我诉说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还能感觉到她眉目间的光芒,感觉到她浑身哗然畅行的光合作用,感觉到她贯通终生的耐心与希望。
葵花地里的最后一轮劳动也结束了,在等待葵花收购的日子里,每天晚餐之后,我们全家人一起出去散步。
真的是全家人——跟屁猫也去,赛虎也去,一只胆大的兔子也非要跟去。
我们这一队人马呼呼啦啦走在圆月之下,长风之中。我妈无比快乐,像是马戏团老板带着全体演职员工巡城做宣传。
我也眷恋那样的时刻。宁静,轻松,心中饱满得欲要盛放,脚步轻盈得快要起飞。那时的希望比平时的希望要隆重许多许多。
我妈走着走着,突然问我:“听说你们城里有买那种隆胸霜的?”
“隆胸?”
“是啊,就是往奶上一抹就变大了的药。”
我瞟一眼她的胸部,问:“你要那个干嘛?”
她得意地说:“我告诉你啊,这可是我想出来的好办法!用那种霜往我们家狗耳朵上一抹,耳朵不就支棱起来了吗?该多神气!”
我一看,果然,我们家大小两条狗,统统都耷拉着耳朵,看上去是挺蔫巴的。
“连个猫都打不过,还好意思支棱耳朵……”
我妈整天操不完的心,狗的耳朵立不起来她也管。公鸡踩母鸡,踩得狠了点儿,她也要干预。猫在外面和野猫打架,她也要操起棍子冲上去助战。每天累得够呛,满脸“队伍不好带”的痛心样儿。
直到这会儿,她才感到事事舒心。在静谧的夜色中,领着全家老小晃荡在空旷的河边土路上,又像一支逃难队伍在漫长旅途中获得了短暂而奢侈的安宁。
我做了个梦,梦见我们仍在月光下散步,这回都到齐了。鸭子也一摇一摆跟在后面。我家新收的葵花籽装麻袋垒成了垛,高高码在拖车上,也慢慢跟着前行。突然又想起还有外婆,我赶紧四处寻找。然后就醒来了。
乡下人难得进一次城,她列了长长的清单。然而什么都嫌贵。最后只买了些蔬菜。
菜哪儿没卖的?但是阿勒泰的菜比富蕴县的便宜。
还买了几株带根的花苗。
天寒地冻的,她担心中途倒车的时候花苗被冻坏,便将它们小心地塞进一个暖瓶里,轻轻旋上盖子。
她每次来阿勒泰顶多呆一天。一天之内,她能干完十天的事情。
每次她走后,好像家里撤走了一支部队。
走之前,她把她买的宝贝花慷慨地分了我一枝。
我家没有花盆,她拾回一只塑料油桶,剪开桶口,洗得干干净净。又不知从哪儿挖了点土,把花种进去,放在我的窗台上。
因为油桶是透明的,她担心阳光直晒下土太烫了,对根不好,特意用我的一本书挡着。
她走后,只有这盆花和花背后的那本书见证了她曾到来。
是的,我最擅长离别。迄今为止,我圆满完成过各种各样的离别。
我送我妈离开,在客运站帮她买票,又帮她把行李放进班车的行李厢,并上车帮她找到座位。
最后的时间里,我俩一时无话可说,一同等待发车时间的到来。
那时,我突然想起来很久很久以前的另一场离别。旧时的伤心与无奈突然深刻涌上心头。
我好想开口提起那件事,我强烈渴望得知她当时的感受。
却无论如何都说不出一句话来。
此时此刻,彼此间突然无比陌生,甚至微微尴尬。
我又想,人是被时间磨损的吗?……不是的。人是被各种各样的离别磨损的。
这时,车发动了。我赶紧下车,又绕到车窗下冲她挥手。
就这样,又一场离别圆满结束了。
最后的仪式是我目送这辆平凡的大巴车带走她。
然而,车刚驶出客运站就停了下来。高峰期堵车。
最后的仪式迟迟不能结束。我一直看着这辆车。我好恨它的平凡。
我看着它停了好久好久。有好几次强烈渴望走上前去,走到我妈窗下,踮起脚敲打车窗,让她看到我,然后和她再重新离别一次。
但终于没有。
有一次我妈打电话给我,非常害怕的口吻:“娟啊,你赶快回家吧,情况有些不对……”
“是不是外婆她……”
“唉,你外婆越来越不对劲儿了,你要是看到她现在的样子,肯定会吓一大跳。天啦,又黑又瘦,真是从来也没见她这么黑过……是不是大限要到了?你赶快回来吧,我很害怕……”
我赶紧回家,倒了两趟车,路上花了一整天工夫,心急如焚。
到家一看,果然外婆脸色黑得吓人,并且黑得一点儿也不自然,跟锅底子似的。
我又凑近好好观察。
回头问我妈:“你到底给她洗过脸没有?”她想了想:“好像从来没有。”……
外婆跟着我时总是白白胖胖,慈眉善目。跟着我妈,整天看上去苦大仇深。
她总是趁我上班时,自己拖着行李悄悄跑下楼。她走丢过两次,一次被邻居送回来,还有一次我在菜市场找到她。
那时,她站在那里,白发纷乱,惊慌失措。当她看到我后,瞬间怒意勃发。似乎正是我置她于此处境地。
但却没有冲我发脾气,只是愤怒地絮絮讲诉刚才的遭遇。
有一次我回家,发现门把手上拴了根破布,以为是邻居小孩子恶作剧,就解开扔了。
第二天回家,发现又给系了一根。后来又发现单元门上也系的有。
原来,每次她偷偷出门回家,都认不出我们的单元门,不记得我家的楼层。对她来说,小区的房子统统一模一样,这个城市犹如迷宫。于是她便做上记号。
这几块破布,是她为适应异乡生活所付出的最大努力。
在阿勒泰时,我白天上班,她一个人在家。每天下班回家,一进小区,远远就看见外婆趴在阳台上眼巴巴地朝小区大门方向张望。她一看到我,赶紧高高挥手。
每天我下班回家,走上三楼,她拄着拐棍准时出现在楼梯口。那是我今生今世所能拥有的最隆重的迎接。
每天一到那个时刻,她艰难地从她的世界中抽身而出。在她的世界之外,她放不下的只有我和赛虎了。我便依仗她对我的爱意,抓牢她仅剩的清明,拼命摇晃她,挽留她。向她百般承诺,只要她不死,我就带她回四川,坐火车回,坐汽车回,坐飞机回,想尽一切办法回。回去吃甘蔗,吃凉粉,吃一切她思念的食物,见一切她思念的旧人……但是我做不到。一样也做不到。
我妈把外婆接走那一天,我送她们去客运站,再回到空旷安静的出租屋,看到门把手上又被系了一块破布。终于痛哭出声。
我就是一个骗子,一个欲望大于能力的骗子。而被欺骗的外婆,拄着拐棍站在楼梯口等待。她脆弱不堪,她的愿望也脆弱不堪。我根本支撑不了她,拐棍也支撑不了她。其实我早就隐隐意识到了,唯有死亡才能令她展翅高飞。
我觉得外婆最终不是死于病痛与衰老的,而是死于等待。
几乎每个母亲都有自己的拿手菜,几乎每个孩子对母亲的怀念里都有食物的内容。
我虽然是外婆带大的,但和我妈也共同生活了不短的时间,可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她给我做过什么好吃的。
我妈除了做饭难吃这个特点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她做的再难吃的饭她自己都能津津有味吃下去。
总之谁和她过日子谁倒霉。
我记得小时候,有好几次,吃饭吃到一半就忍不住吐了。
对此,我妈的态度总是:“爱吃吃,不吃滚。”
幸亏有外婆。虽然外婆在养育孩子方面也是粗枝大叶的人,但在吃的方面从没委屈过我。
一想起外婆,对土豆烧豆角、油渣饺子、圆子汤和莲藕排骨汤的记忆立刻从肠胃一路温暖到心窝。
我一口一口吃着眼下这一大盆用豆瓣酱煮的青菜叶,恍惚感到,外婆死后,她有一部分回到了我妈身上。
或者是外婆死了,我妈最坚硬的一部分也跟着死了。
吃完这顿简单的午饭,我妈开始和我商量今后的打算。
我也为外婆写了一份悼辞:秦玉珍,流浪儿,仆佣的养女,嗜赌者的妻子,十个孩子的母亲。大半生寡居。先后经历八个孩子的离世。一生没有户籍,辗转于新疆四川两地。七十多岁时被政府召回故乡,照顾百岁高龄的烈属养母。拾垃圾为生,并独自抚养外孙女。养母过世后,政府提供的六平米的廉租房被收回,她于八十五岁高龄独自回到乡间耕种生活。八十八岁跟随最小的女儿再次回到新疆。从此再也没能回到故乡。
今年是种地的第二年,她算是很有经验了,从地边的日常生活到田间管理,都比去年省心了许多。
但今年的大环境却更恶劣,旱情更严重,鹅喉羚的侵害更甚。
她一共补种了四茬葵花,最后存活的只剩十来亩,顶着刚绽开的小花盘,稀稀拉拉扎在荒野最深处。
附近远远近近十来家种植户,多则承包了上千亩,少的也有两三百亩。像我妈这样种了不到一百亩的独此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