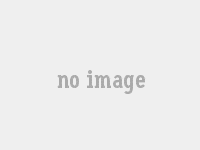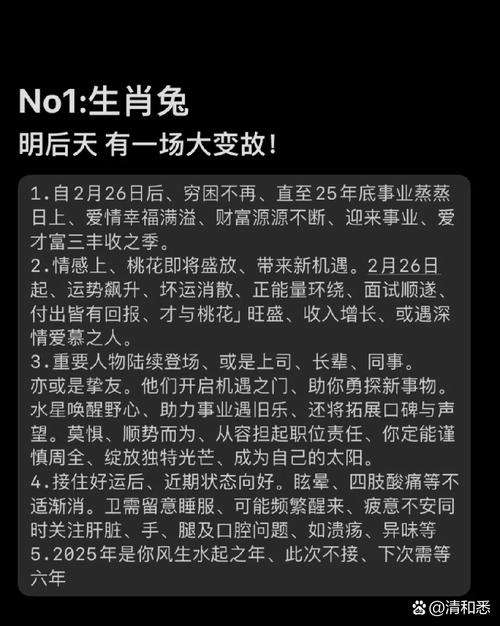80年接兵,我对路遇的一个青年人说:“走,到部队打篮球去”
我营区离县城可有十多里山路,不通公交,得走上大半天。
"连长说话算话吧?"他问得小心翼翼,生怕我不认账似的。
那会儿我才三十出头,被叫连长总觉得自己老了十岁。
可这么一问,我还真不好意思说不算数。
"算话!当然算话!"我拍了拍胸脯,"你叫啥名字?来,进来打球。"
"马建国。"他跟着我进了营区,脸上的笑容像刚拿了糖的孩子。
营区里的战士们看见生面孔,都好奇地围过来。
马建国有些拘谨,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手里的帆布包捏得紧紧的。
"这是来跟咱们打球的,县一中的马老师。"我一介绍,大家热情地打招呼。
就这样,马建国成了我们连队的"编外战友"。
每到周日他准时出现,不管刮风下雨,穿着那双开胶的解放鞋,背着那个破旧的帆布包,在我们的水泥篮球场上跑得比谁都欢。
渐渐熟了,我才知道马建国是县一中的代课老师,每月工资才四十多块钱。
他球打得好,动作规范,投篮那个准,简直就是个半路出家的"篮球专家"。
我问他在哪学的,他憨厚地挠着头发笑:"自学的,看书学的,还有电影里看到的。县里没啥像样的篮球场,都是在土地上随便搭的架子,看到你们这场地,那水泥地面,那漂亮的篮圈,可把我眼馋坏了。"
他说这话时,眼神里满是向往,像个孩子看着心爱的玩具,充满了纯粹的快乐。
战士们都喜欢他,喊他"马老师"。
有时候休息,他会讲些课堂上的趣事,那张嘴能说会道,逗得大家前仰后合。
他嗓门不大,但说起话来有股感染力,声调忽高忽低,像在唱歌,听着就舒服。
"马老师,你这双鞋该换了。"新兵小王总爱打趣他,指着他那双开胶的解放鞋。
马建国摆摆手:"这鞋结实,穿着踏实。"
说着,还特意抬起脚来展示那双已经开裂的鞋底。
小王不解:"才几十块钱一双布鞋,你舍不得?"
马建国笑而不语,只是岔开了话题:"来来来,继续打球。"
我们几次想送他双球鞋,都被他婉拒了。
"有那闲钱,你们还是给老兵买点好烟抽抽。"他总这么说。
那时候的马建国在我眼里,就是个爱打球的普通代课老师,总是笑呵呵的,像是生活中没有什么烦恼。
直到那次意外发生。
那天是连队对抗赛,马建国作为"客队"和几个战士一队,场上气氛热烈,小战士们为了在马老师面前表现,个个使出浑身解数。
马建国带球突破,过了两个人,眼看就要上篮,忽然脚下一软,整个人栽倒在地,脸色煞白,嘴唇发紫,豆大的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滚。
"马老师!"大家齐声惊呼,立刻围了上去。
我一摸他额头,冰凉冰凉的,眼睛已经闭上了,意识不清。
给他枕上衣服,掐人中,可就是不醒。
我一看这情况不对劲,立马招呼通讯班的开车,把他送进了县医院。
等送到医院,大夫检查后说他是先天性心脏病,轻微二尖瓣脱垂,不能做剧烈运动。
"这些年能踢能跳没出大事,算是运气好,要是再来几次这样的剧烈运动,后果不堪设想。"大夫严肃地说。
"以后打球可得悠着点了,太累了容易出事。"大夫叮嘱道。
马建国听完,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精气神,眼睛里的光暗了下去。
他躺在病床上,望着天花板,半天没说一句话。
那一刻,我第一次看到了他眼里的绝望。
第二天,我领着小王和通讯班的老李去他住处看望。
马建国出院了,但大夫说要静养几天才能去学校上课。
我们沿着县城边缘一条泥泞的小巷,七拐八拐,走到尽头一间低矮平房前。
破旧的砖墙上爬满了青苔,窗户上糊着发黄的报纸,掉漆的木门看起来摇摇欲坠。
敲了半天门,才听见里面有人应声。
"马老师,我们来看你了!"我喊道。
推开掉漆的木门,屋里暗得让人一时看不清东西。
等眼睛适应了,我才发现这是间不足十五平米的屋子。
靠墙是张旧木床,一个瘦骨嶙峋的老人瘫在上面,身边坐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扎着两个羊角辫,穿着打了补丁的蓝布褂子。
马建国站在窗边,有些尴尬地看着我们。
"坐吧,没什么好招待的。"他搬出几个低矮的板凳。
角落里摆着几本发黄的教科书和一摞批改了一半的作业本,床头柜上一个搪瓷缸里插着几支钢笔,墙上贴着几张褪色的篮球明星剪报,那是马建国的全部家当。
"这是俺爹,这是俺妹妹小雨。"马建国介绍道,声音里带着从未有过的疲惫。
"你们好,你们好。"老人的声音虚弱,但客气,费力地抬起那只能动的右手。
小雨羞涩地点点头,赶紧去烧水倒茶。
我这才明白他为什么总拒绝我们的好意。
他不是不需要,是真的接受不起。
他挑起整个家,瘫痪的父亲,上学的妹妹,全靠他那点微薄的代课费。
"爹,前年得了脑血栓,半边身子不能动了。"马建国轻声说,"小雨还上初中,学习挺好的,我想让她考高中,将来有出息。"
他的话不多,但每一句都沉甸甸的,藏着太多的艰辛和负担。
小雨泡了茶,是用瓦罐煮的大麦茶,苦涩中带着甜味。
"马老师,医生说的话,你听到了吧?"我轻声问道,心里已经打定主意要帮他。
"听到了。"马建国勉强笑了笑,"看来以后不能打球了,挺遗憾的。"
他说得平静,但眼神里的失落却怎么也掩饰不住。
球场是他的乐园,是他为数不多的快乐来源。
现在连这个都没了,他还能有什么?
晚上回营房,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马建国家那昏暗的灯光和他黯淡的眼神。
"连长,也不知道马老师家里咋这么困难,他咋不早说呢?"小王也睡不着,翻过身子小声问我。
"男人嘛,都要面子。"我叹了口气,"何况他是老师,更要脸面。"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找了政治教导员商量。
教导员是个四十多岁的老同志,打过仗,经历过困难时期,最是明事理。
没等我说完,老教导就拍板:"组织个捐款,给马建国家帮把手。马老师为人好,球打得也好,这么些日子没少带咱们的兵打球,现在人家有难,咱们不能袖手旁观。"
战士们听说马建国的情况,不用动员,自发把津贴都掏了出来。
谁的钱都不多,可积少成多,也凑了一百多块钱。
我拿着钱去看马建国,他刚从学校回来,脸色还有些苍白。
"马老师,这是连队战士们的一点心意,你收下。"我把钱递给他。
马建国看了眼信封,脸色一变,死活不肯收,说什么也不行,急得满脸通红:"这不合适,真不合适。我不需要,真不需要。"
他越是推辞,眼圈越红,像是忍着什么巨大的委屈和痛苦。
眼看着他要急火攻心,我灵机一动:"那这样,你来当我们文艺宣传队的指导员,每周来两次,算是工作报酬,总行了吧?我们连队要参加师里的文艺汇演,正缺个有文化的人来帮忙呢。"
马建国听完,静了好一会儿,眼圈红了。
这个三十出头的大男人,在我面前眼泪差点掉下来。
"行,这个活我接了。"他声音哽咽,"不过工钱得按劳取酬,不能多给。"
就这么说定了。
有了这层关系,我们更方便照顾他家。
战士们轮流去教小雨功课,帮着照顾马老汉,连队的军医还专门给老人看病开药。
我发现马建国虽然不能打球了,但他有别的才能。
他讲课是把好手,还会写文章,偶尔在县报上发表几篇散文和小故事。
有回我去他学校听课,就见他讲《水浒传》,那叫一个活灵活现,学生们个个听得入神。
他那时候穿着件褪色的蓝衬衫,站在讲台上,明明那么瘦,却像有使不完的力气。
说起武松打虎,他手舞足蹈,眉飞色舞,教室里静得能听见呼吸声。
下课铃一响,娃娃们还围着他问这问那,哪有半点想走的意思。
"马老师,你讲得真好!"我由衷地称赞。
"教书匠嘛,说书唱戏的把式还是有一点的。"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正巧我有个老战友张明转业到了教育局,当了干事。
我一合计,带马建国去见他,想帮他争取个正式教师的名额。
"代课老师转正,没文凭可不行啊。"张明为难地说,"上头卡得紧,必须是大专以上学历才能考虑。"
马建国低着头:"我只上过中专,没考上大学。"
他的声音很轻,但我听出了其中的苦涩。

回去的路上,马建国沉默不语。
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像是也在叹息。
"没考上大学,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他突然开口,"当年高考,我差了两分,眼睁睁看着梦想破灭。要不是为了养家,我早就再复读一年了。"
我拍拍他的肩膀,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谁知道第二天他来连队找我,眼里又燃起了光:"刘连长,我想考大专,拿个文凭!"
"好啊!你要有这个心,我支持你!"我一拍大腿,"咱们连队还有不少高中课本,你可以拿去用。"
"我已经打听好了,省师范学院有函授班,可以边工作边学习。"他兴奋地说,"就是学费有点贵,得三百多块钱。"
"这个钱,我给你垫上。"我不假思索地说。
"不行!"他连连摇头,"那是你的血汗钱。"
"那这样,你在连队当文艺指导员的工资先预支一年,够不够交学费?"我想了个折中的办法。
马建国愣了一下,眼眶又红了:"够了,够了。"
从那以后,马建国成了两头忙的人。
白天教课,晚上学习,周末还来连队当文艺指导员。
他虽然不能打球了,却教出了不少篮球好手。
连队里原本打球的没几个,在他的指导下,竟有模有样地组成了队伍,还在师里的比赛中拿了名次。
他编排的文艺节目也颇有特色,不是那种千篇一律的歌舞,而是根据连队实际情况,自编自导的小品和朗诵,真实感人。
我们连队组织军民联欢会,马建国编排的节目多次获奖。
慢慢地,县里有了名气,教育局的领导都注意到他了。
可家里的日子还是紧巴巴的。
小雨考上了高中,学费比初中贵多了。
老人的病也时好时坏,常年吃药,开销不小。
马建国自己也累得不轻,脸上的笑容少了,眼里的疲惫多了。
有时候我去他家,看到他伏在煤油灯下念书,嘴里念念有词,身边是熬夜批改的作业本和备课笔记。
"马老师,你这样熬身体吃不消啊。"我心疼地说。
"没事,我命硬着呢。"他揉揉眼睛,笑着说,"再苦再累,也比当年差两分没考上大学强啊。这回我一定要拿到文凭,给小雨做个好榜样。"
就是这样的毅力,支撑着他一步步走了过来。
一九八三年夏天,马建国捧着录取通知书来找我,脸上的笑比当年在火车站第一次见面时还要灿烂。
他考上了省师范学院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可以带薪进修。
"刘连长,要不是你那句'走,到部队打篮球去',我现在可能还在那个小屋子里做着白日梦呢。"他感激地说,眼里闪着泪光。
"什么白日梦啊?"我好奇地问。
"当年我看着表弟去当兵,心里那个羡慕啊,想着自己要是能换个环境,人生会不会不一样。"他笑着说,"结果还真被你这一句话改变了命运。"
"说啥谢不谢的,都是战友。"我拍拍他的肩膀,心里却满是欣慰。
马建国进修期间,连队的战士们接力照顾他家。
小雨考上了高中,学习成绩优异,老人的病情也稳定了不少。
一九八五年,马建国拿到了大专文凭,正式转为公办教师。
薪水提高了一倍不止,日子总算有了奔头。
同年秋天,我接到调令,要去边疆部队任职。
临行前,我组织了一场特殊的军民联谊篮球赛。
马建国带着他在学校教出来的学生球员,和我们连队的战士同场竞技。
他站在场边,不再像当年那样风风火火地在场上奔跑,但眼里的光彩一点不减。
他的学生们个个生龙活虎,打得有板有眼,把连队的小伙子们压得喘不过气来。
比赛结束后,我宣布了一个好消息:经过连队和县教育局的共同努力,马建国所在的学校将建一个标准篮球场,由他担任学校体育教研组长。
这个消息一出,大家都欢呼起来。
马建国站在那里,泪流满面,嘴唇颤抖着说不出话来。
"我不能打球了,但我可以教别人打球,这样一样快活。"半晌,他才找回自己的声音,眼里闪着光。
分别的时候,马建国送我到车站,就像当年我在车站接新兵一样。
"刘连长,你放心去边疆,这边有我呢,战士们家里有啥事,我帮着照应。"他拍着胸脯保证。
"那就麻烦你了,马老师。"我握着他的手,心里满是不舍。
一九九五年,我探亲归来,特意去县一中找马建国。
学校大变样了,崭新的教学楼,漂亮的篮球场,远远看见穿着运动服的马建国正带着学生训练。
他两鬓已有了白发,但站在阳光下的背影,依然挺拔如松。
"马教练!"我喊他,声音里带着十年未见的思念。
他猛地转身,愣了半晌,忽然大笑着跑过来:"刘连长!真是刘连长!"
我们紧紧拥抱,像是回到了当年在篮球场上挥汗如雨的日子。
"你瘦了。"他拍着我的肩膀。
"你胖了。"我笑着说,看他气色红润,身材结实,哪还有当年那副病恹恹的样子。
当晚,马建国非要摆酒,说是庆祝我回来。
酒桌上我才知道,这些年他的变化有多大。
他从一个普通的代课老师,成了县里小有名气的教育工作者。
他编写的《篮球教学法》在省里获了奖,学校的篮球队连续三年获得市里的冠军。
小雨也考上了师范学院,毕业后回到县一中当了老师,还嫁给了一个老实巴交的木匠。
老人的病情稳定了,虽然还是瘫痪,但有了专人照顾,日子过得舒心多了。
马建国自己也结了婚,娶了同校的一个语文老师,小两口感情好得很。
"好啊,好啊。"我由衷地为他高兴,想起当年那个站在哨亭边上,手足无措的高个子青年,再看看现在这个自信从容的中年人,心里满是感慨。
"刘连长,我们连队的篮球场还在吗?"马建国突然问道。
"在啊,虽然翻新了,但地方没变。"我说。
"那咱们去看看?"他眼里闪着光,像个孩子。
就这样,我们回到老营区,那个水泥篮球场早已翻新,却依然是我们记忆中的模样。
夕阳映照下,球场上几个年轻战士正在打球,青春的汗水在金色的阳光中闪闪发光。
"刘连长,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马建国拍着篮球问我,声音里满是怀念。
"记得,火车站,你送表弟参军。"我笑着说,那一幕仿佛就在昨天。
"那时候我在县城找不到像样的篮球场,听说部队有标准场地,眼馋得很,可就是没机会进来。"他笑着摇头,"后来你随口一句话,我就赖上你了。"
"走,到部队打篮球去。"我重复着那句话,恍如隔世。
"就是这句话,改变了我的命运。"马建国望着落日,声音里带着感慨,"那时我家里困难,爹瘫痪,妹妹上学,我就那点代课费,日子难过。我喜欢打球,可县里没场地,心里窝着股劲儿没处使。后来在这个篮球场上,我找到了不一样的人生。"
他说着说着,眼眶湿润了。
"我记得当初你不能打球时,那个失落的样子,像是世界末日一样。"我轻声说。
"可不是嘛,那会儿我觉得天都塌了。。每次日子难过,我就想着周日能来部队打球,那种期待支撑着我熬过一周。突然说不能打了,我真的崩溃了。"
"可你挺过来了,还找到了新的出路。"我拍拍他的肩膀。
"多亏了你们啊。"他转过身,动情地说,"刘连长,谢谢你。"
"说啥谢不谢的,都是战友。"我拍拍他的肩膀,"来,咱们再投几个。"
虽然马建国不能剧烈运动,但投几个球还是没问题的。
我们俩轮流投篮,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健步如飞,但每一投都饱含着对过往岁月的珍重。
"你还记得那会儿,你第一次来,穿着一双开胶的解放鞋吗?"我笑着问。
"可不嘛,那双鞋我穿了三年,舍不得换。"他也笑了,"那会儿攒钱给爹看病,给小雨交学费,哪有闲钱买新鞋啊。"
"你每次来,小王都要损你两句。"我想起那个爱开玩笑的小战士。
"小王后来咋样了?"马建国问道。
"转业了,去了南方一个厂子,听说当上车间主任了。"我说着,把球传给他。
"那小子机灵,肯定有出息。"马建国点点头,接过球,稳稳投入篮筐。
我们你一言我一语,回忆着过去的点点滴滴,脸上满是笑容。
最后一球,马建国拿在手里,没急着投。
"刘连长,我时常想,如果当年没遇见你,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他望着远处的夕阳,眼里有光。
"可能还是老样子吧,教书,养家,日子虽然清苦,但也过得去。"我说。
"不会的。"他摇摇头,"没有你们,我可能早就被生活压垮了。是你那句话,给了我希望,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可能。"
说完,他举起球,稳稳命中。
球划过夕阳,带出一道优美的弧线,"唰"的一声落入篮网。
"走,到部队打篮球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