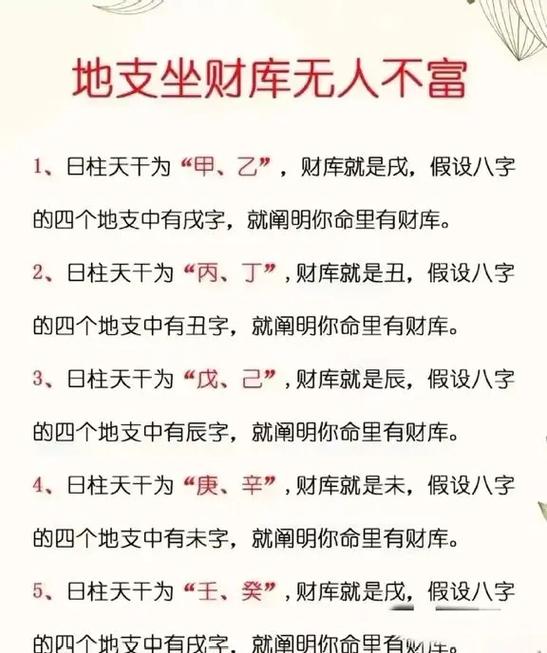一文||【陪伴母亲的日子(3)】母亲说她活不了多久了
【年近九十,母亲的老年痴呆日益严重,伴随轻度中风,生活不能自理。我放下手头的工作陪伴着她,并将她的焦虑、挣扎、痛苦和快乐记录下来。】
(2016年,母亲81岁)
1.
上午往往是母亲的状况比较糟糕的时段,多数时候处在恍惚中。在恍惚中醒来,在恍惚中吃早餐,早餐后又在恍惚中睡去。睡醒了,午饭的时间也到了。她在午餐时间和下午是最清醒的时候,晚上又会进入恍惚的状态。
今早一起来却精神很好,像打了鸡血一样。还没下床就传来“我们的台湾一定要解放”的歌声,接着一边扭动着腰肢一边踏着节奏走出房门。
早餐吃的馄饨,昨晚逛商场时儿媳妇买的,她每天都变换着花样给老太太不同的餐食,麦片,稀饭,肉食,蔬菜,水果,是每天的标配,一个鸡蛋、一盒鲜奶则是雷打不动。儿媳妇买的东西母亲就吃得特别带劲,有时还边吃边念叨是谁谁谁买的。
吃饭时她坐在我对面,边吃边唱着她最喜欢的那首“解放台湾”的歌,一遍又一遍。唱的时候双手举过头顶,在空中舞动,双脚也没闲着,在地上打着拍子。除了这首歌,她经常唱的还有“肚子饿得叽叽地叫”和“地主恶霸是豺狼”。不过,这两首歌听她唱了无数遍,除了第一句词,后面的词都辨不清唱的啥。
我让她反复唱这两首,儿媳妇和保姆秋芳我们三个人一起分辨歌词。终于听出来“肚子饿得那叽叽地叫”后面两句是“duo re mi fa suo”和“肚子辣得冇奈何呀!”老家的方言中,“肚子辣”就是“肚子饿”,这句话的意思是“肚子饿得实在是无法忍受呀!”。而“地主恶霸是豺狼”后面是“你不杀他他咬人”。
吃完饭,收捡好碗筷,刚弹了会琴,妻走过来神秘地对我说,母亲坐在书房的藤椅上看书,竟然是我们摆在桌上的《新雅思精讲》。我蹑手蹑脚来到书房门口,母亲果然在看书,我知道她看不懂书上的英文,一个字母也不认识,可那全神贯注的样子,丝毫不亚于一位备考的大学生。
(母亲走向书房)
我猜她坐在这里,并不是来看书的,而是为了看窗外的校园和校园围墙外的小路。早晨的太阳透过玻璃,洒在蚂蚁般密密麻麻的外国文字上,屋子里充满着春天温暖的味道。
母亲经常坐在书房宽大的玻璃窗前,望着窗外的校园和校园围墙与我们住的楼之间的那片菜地里弯弯曲曲的小路,她说自己是走那条路从老家来到这里的,她的孙子在那所学校读书。
看着母亲读书的样子,颇觉滑稽,凑近她笑着说:“好,这样坐着舒服,看看书,累了就靠着睡睡。”母亲似乎很开心:“是的,这里很舒服。外面很好看。”
转眼,母亲真的靠在椅子上睡着了,妻将自己的长大衣盖在她的身上,出去办事了。暖阳洒在母亲的脸上,安然自在。
2.
母亲睡着的当儿,我开始练琴。我今天练的是小汤普森(3)的练习曲《假日之歌》。弹了几遍,站起来去拿茶杯,发现母亲不知什么时候醒了,离开书房,坐到餐桌旁的椅子上来了,右手撑在拐棍上。
我拿起茶杯,喝了一口,以为母亲在听我弹琴,望了她一眼,继续弹我的琴。练了三四遍,回头一看,母亲还是刚才那个姿势一动不动地坐着。我从钢琴凳上站起来,走近她。母亲面无表情,眼睛直直地盯着餐桌桌面,眼睛里已经没有了生机,只有无边的暗淡。
(母亲的眼睛里只有无边的暗淡)
我叫了一声“妈”,没有反应,只看见她的眼睛眨了一下。摸摸她的手,冰凉;抚摸她的脸,没有反应。她像一尊雕像静静地摆在那儿,除了眼睛的眨动,其它都是静止的,似乎进入了一个黑暗而冰冷的世界,灵魂已经飘到了某个遥远的地方。从她那眨动的眼睛里,我分明感觉到她还在尽最后的努力,耗尽最后一点力量挣脱那个黑洞巨大的引力,想回到这个有光和声音的世界里。
她的大脑的某根血管又堵住了。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已经是三年前了。那天早餐后,她甩着胳膊在家里走着。边走边大幅度前后摆动手臂,这是她状态好的时候走路的标准动作。
突然,她停住了,一只胳膊还停在空中没有收回来。就像一个机器人,正在摆动双手,大踏步前进,突然没电了,迈开的双脚像被钉子钉在地上,不能动弹,胳膊静止在半空中,收不回来。幸好在她耗尽最后一点维持平衡的力气倒下之前,保姆眼疾手快,跑过去扶住她。
救护车把她送到医院,CT,核磁共振,各种检查,脑萎缩,脑血管狭窄,但终究找不到血管堵塞的具体位置,不能做出脑梗的诊断。在医院趟一个多小时醒来,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也没有什么后遗症。
这次之后,隔一段时间就发生一次。开始时每次都叫救护车送医院,照例是各种检查,照例是找不出具体原因,照例是昏迷一两个小时就醒来。说是血管狭窄造成缺氧,那平时也一直狭窄,为什么不昏迷呢?一般认为应该是某个地方堵塞了才会出现这种现象。可怎么也找不到具体堵塞的位置。医生也说不出所以然。开始一两次还给她打融栓针,后来也不打针了,医生检查完后就让她睡,睡一两个小时又好了。
我在网上看到脑梗的急救知识,一是掐拇指与食指之间的虎口,二是拍胳膊肘弯。在送了几次医院后再出现突然昏迷的情况时,我们就让她平躺在家里的床上或沙发上,不垫枕头,掐她的虎口。果然,掐几下她就会有反应,喊痛,或者自己把手抽开,有时还怪我们吵她的瞌睡,说我们欺负她,不让她睡觉。只要她有了反应,我们就会放心让她继续睡。
3.
我和秋芳一起把她抬到沙发上躺下。一躺下,她的眼睛立刻闭上,进入深睡状态,手脚冰凉,浑身僵直。叫她,没有任何反应。掐虎口,不像平时会叫,这次也没有反应。掐了几次,没有反应,力度不断加大,直到虎口掐青了,还是没有反应。我用力拍她的肘弯,没有反应。我们热了两个热水袋,一个放她脚头,一个放在胸口。
母亲平躺在那里,僵硬挺直,双手摆在身体的两侧,眼睛紧闭,嘴唇微微曦开,脸上的皮肤死灰一般,像是一张脱离了血管和肌肉连接的皮覆盖在木头雕刻的人脸模具上。刚刚挣脱冬天的乌云束缚的春日斜斜地从窗户射进来,洒在母亲的脸上和覆盖着她身体的被子上,增添了些许温暖。
我站在她的脚头看着这副景象,心里颤栗了一下,死亡的念头在我脑海中闪过,母亲会不会再也醒不过来。秋芳仍然坐在母亲身边,一只手搭在母亲的肩膀上,似乎想摇醒她,又害怕惊着她,眼睛六神无主地看看躺着的人,再看看我,恐惧的阴影笼罩在她的脸上。
“昨天晚上她比平时睡得晚,很兴奋,跟我唠叨了很久,说了很多事。她还笑着说自己活不了多久了。”秋芳一定是有种不祥的预感,在我们老家,如果老人跟别人说自己活不了多久了,往往都很灵验。寿命越长的人越能预感自己死的时间。
听秋芳这么一说,加上早上起来母亲那种反常的兴奋劲,我自然想起“回光返照”这个词。
为了掩饰自己内心的慌乱,我开始在屋子里慢慢地踱起步来。同时安慰秋芳:“别慌,睡一阵就会醒来的”。心里却在想,是叫救护车还是让她继续睡下去。继续睡下去万一醒不来,又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期。脑梗的抢救有效时间是发病后六个小时,也有说四个小时的,当然是越快越好。不过,母亲这种状况,医生也不敢下定论是不是脑梗。
母亲接连几次从突然昏迷中醒来的折腾后,我有一种预感,终究会有一次,她再也不能从这种昏睡中醒来。现在,此刻,看着她这样安宁地躺着,心里又不忍去打扰她,也许她真能这样走了,倒是她老人家的福气。
是呀,让她躺着吧。我走近她身边,摸了摸她的脸,有温度,没反应,安然得像照在她脸上的阳光。
4.
我转身坐到钢琴前,继续弹奏刚才的《假日之歌》。曲子温柔、恬淡、轻松。也许母亲太累了,让她听着这美好的音乐休息吧。有那么一刻,一个念头在我脑子里闪过,母亲的灵魂会不会随着这音乐飘向天堂,再也不回来?
这些年来,母亲一直在和自己的大脑搏斗。大脑像个黑洞,一步步,一点点,把她的记忆、她的个性、她之所以为她的一切东西都吞噬掉。而她极力把它们拽回来。这是一个人的战争,自己与自己的战争。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她一天天陷落,谁也帮不了她。
现在,她好像妥协了,她用她的沉睡向那个黑洞般的大脑宣布投降了。
“我累了,我斗不赢了,我无能为力了。干脆让那个黑洞把我的肉体也吞噬了吧!”
弹着弹着,心里倏然涌出一股孤独的感觉,随之而来的是恐惧。孤独和恐惧随着每次琴键的敲击在不断增强,将音乐中漂浮的温柔和恬静一扫而空,直至双手停在琴键上再也抬不起来。
我想起琼.狄迪恩在《奇想之年》一书中写的一段话:“我爸爸去世于85岁生日前夕,妈妈去世于91岁生日前几个月,两人在去世之前都度过了好几年的渐渐衰弱的过程。他们离开的时候我感到非常难过、非常孤独(不管孩子年龄多大,在被父母舍弃时都会感到孤独),为以前的时光,没有说出口的话,为不能分享的,乃至不能用一切现实的手段表示的感谢,为他们在生命最后那段时间所忍受的痛苦、无助、生理上的羞耻感,为所有这一切感到后悔。”
不行,不能让母亲这么走了,不管她走的时候多么安详,我都不能忍受失去她的孤独和痛苦。
我霍然从琴凳上站起来,奔向母亲躺着的沙发,在她身旁蹲下,把她的右手从被子里抽出来,摆平,用力在她的肘弯处啪啪啪地连续拍打。不知拍打了多少下,母亲突然惊醒,大声说:“谁在打我!”
我深深地噓了口长气,如释重负,带着失而复得的狂喜站起来,开心地笑着说,“我打你,懒虫,饭都熟了,还不起来吃!”
还有一句“再打不醒你就叫救护车了”到了嘴边又吞回去了。不想让她觉得有什么不正常。
她也咯咯笑起来,举起双手,伸展着十指,伸向我。见此,一股温情涌上心头,母亲这时就是个孩子,醒来时,看见守候在床边的父母,伸伸懒腰,伸出双手,幸福地搂着父母的脖子,随着父母渐渐伸直的腰杆,离开枕头,起身坐起来。
我抓住她的双手,边拖边说:“乖乖,起床吃饭了。”自从母亲得了老年痴呆,我和她的关系不知不觉中颠倒过来了,她变成了孩子,我像是父亲。
给她穿上鞋子,把拐棍递给她。她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摇一摆地往餐桌去了。
美国著名的环境哲学家、“国家公园之父”约翰•缪尔曾经这样描述死亡:“让孩子们与自然同行,让他们看到死亡与生命的美丽交流和交融......他们将懂得死亡没有刺痛感,和生命一样美丽。”

我也曾想,在悠扬而飘渺的音乐里溘然沉睡,再也不醒来,这种死亡也许是一种美丽。可当想到这个不再醒来的人是母亲时,心里还是会刺痛,怎么也看不到死亡与生命的美丽交流和交融。
5.
一会儿,秋芳就把午餐摆到桌子上。不像往常,吃午餐的时候一般情绪都比较好。此刻,她坐到餐桌边的椅子上,默不作声,没有食欲。劝她吃饭,她默默地坐在那里,只是摇头。我只好将她的饭碗拿过来,用饭匙一口一口送进她的嘴里。
“不吃会饿死的,情愿被胀死,也不要当饿死鬼呀!”我边喂边哄,母亲并不抗拒,木然张嘴,木然嚼咽,好不容易吃完了饭。稍停片刻,她吃力地站起来,举着拐棍,一步步向卧室挪去。
“又去睡呀?”秋芳追过去,扶着她进了卧室。
这次没有睡太久,大约半个小时醒来。母亲睡着的时候,我在她房间外面的阳台上看书。她醒后,我让她坐在阳台上的轮椅里。楼下院子里树木环绕的草地上,一群小孩正在叽叽喳喳地玩耍,有的在互相追逐,有的三两个围在一起,席地而坐,似乎在玩弄着草地上的小虫子。
母亲问我这是哪里。我告诉她这是武汉。
“你的崽不是也在这里吗?”
“是的,昨天你还见过咪咪勒。”
“哦,咪咪,好高好高的。还有那两个老的呢,他们也都老了,还利害吗?”
咪咪是我在旁边学校读初三的小儿子,十五岁,已经一米八几的个头。昨天是周日,咪咪一般周五放学回家,周日晚饭后回校。
“那两个老的”指我的岳父母,他们住在汉口,离我们所在的江夏四五十公里。“利害”在我们老家话里是身体健康的意思。
我们就这么你一言我一句地闲扯着。在母亲清醒的时候,她也能记起一些人和事,但这种时候太少了。大多数时候,她连我是谁都不清楚,时时指着我问保姆“这是哪个”。
她望着远处,说那里有条河。我循着她指的方向看去,没有看到河,只看到了一条新铺的柏油马路。
母亲静静地望着窗外,我的视线移到我的书上。没过多久,抬头一看,她坐在轮椅上又睡着了。
(母亲穿着黄色的羽绒服)
母亲穿着一件黄色的羽绒衣,手里抱着热水袋。阳光覆盖了她的全身和轮椅,脸正对着射进来的阳光,光线在她的脸胧上洒上了一层柔和而温暖的光晕。
看她睡得那么安宁,我不忍心打扰她。虽然今天她的瞌睡实在太多了,应该不让她睡了,但她那舒服的样子,仿佛已经进入了太阳永不落下的天国,她在那儿享受着无忧无虑的惬意。
6.
我继续看我的书。阳光照射在洁白的纸上,有些刺眼,但我不忍移动,怕惊醒甜睡中的母亲,怕扰动她那静谧的世界。
我看的是格雷格.奥布莱恩的《一个阿尔兹海默病人的回忆录》。格雷格是美国著名调查记者、作家、编辑和出版人,他的父亲和母亲以及外公都是阿尔兹海默症患者,他也在五十多岁就被诊断为早发性阿尔兹海默症。
发病之后,格雷格凭借非凡的勇气和才华,将自己的尚未丢失的记忆和对疾病的完整体验尽可能记录下来,不仅教会患者如何与疾病“战斗”,也教会普通读者如何“不放弃”生活。
格雷格知道他自己得了什么病,而我的母亲却不知道。格雷格知道自己来到了悬崖边,知道自己被判了死刑,我的母亲不知道。母亲只是在无声无息中悄然掉进了无底深渊,她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处在记忆的黑暗深渊了。偶尔,她会说,“我这个老笨蛋,什么都不记得,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们从来不告诉她这是病,不让她知道她的记忆和认知能力被一个魔鬼吃了。只是安慰她,人老了都这样。这句话让她安然接受这个现实。有时我也会想,这样一种无知的状态,不知对她是仁慈还是残酷。
7.
阳台正对着小区的中央花园,花园的中央那颗玉兰树已经被盛开的花朵包围,像被洁白的纱布裹得严严实实。
洁白的玉兰花本是纯洁和馨香的象征,此时此刻,我却又想起了死亡。上午看着母亲直挺挺躺在那里,我想起了死亡。人死了,也是这样躺着的。那时的死亡给我带来恐惧,恐惧失去母亲。现在看着玉兰花想到死亡时,恐惧被安宁代替了。也许是眼前的母亲那安然的睡眠和温暖的阳光带给我内心的宁静。
在老家过春节期间,一个远房的堂哥因胰腺癌死了,棺材外面的棺罩扎着的白花就像这盛开的玉兰花。
在湘西,哪家死了人,村子里的人都会去守灵,帮助料理后事,这些人都可以在死者家里吃几天的饭,直至下葬完毕,这叫“吃豆腐”。如果谁告诉你他去哪儿吃豆腐了,不是说他去那里占女孩子的便宜,而是去奔丧。
其实,吃豆腐时,谁都可以来,帮忙不帮忙都可以来吃。对于叫花子,这时反而像过年了,好吃好喝,不会有人去驱赶他们。灵堂外面,房前屋后,都摆满了八仙桌,桌上的必备菜,除了鸡、鸭、鱼、猪肉,当然还有豆腐,否则怎么叫吃豆腐呢。
堂哥的家离我家很近,只隔了两户人家,也在河涯上。灵堂就设在他家的堂屋里。入殓的棺材放在堂屋的右边,棺材打开一只角,露出死者的头和脸。死者穿着“老衣服”,身上盖着缎面被子。来吊唁的亲戚朋友刚到的时候,一般都会去看看死者的容貌,以示告别,或默然无语,或号啕大哭,或说句安慰的话:“你放心走吧。”
经常在一起玩耍的人也会开个玩笑,“你死了,三缺一了,哪里去找人来替你呢?”据说他死的头天夜里在隔壁家打麻将,打到半夜,第二天凌晨觉得肚子疼,儿子准备送他去医院,从床上背着他走出堂屋的时候,堂哥就扒在儿子的背上咽气了。
灵堂一般设三、五、七天,由先生选定出殡的日子,期间需要请先生选坟地,村里人挖坟坑。出殡时棺材上会罩上一个竹篾编织的棺罩,棺罩的头部站立一只纸做的白鹤,其它地方扎着白花。孝子贤孙从头至脚披一块白布,出殡时走在棺材的前面,走几步跪一下,叫拜路。
母亲知道隔壁死人了,不断地问我们谁死了。告诉她,一会又忘了。有时她会回忆起这个人,他的名字,他曾经住在老村子的什么地方,甚至有一回还说出了他老婆的名字。不过,一转眼,她又会来问你谁死了。
出殡的前一天中午,我从那家吃完午饭回来,没看见母亲在家里。前前后后找遍了都没看见。哪里去了?焦急间,我突然想起一个地方,莫非她到那里去了?
母亲的棺材放在我们家房子左端头与围墙隔出来的狭窄巷子里。老家的习惯是早早地给老人做好棺材,漆上油黑的漆,放在隐蔽处。很多都是老人自己趁着自己还能劳动的时候,自己为自己把寿木做好。棺材就是自己的归宿,随着年龄的增长,年岁渐渐老去,对自己的棺材会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眷恋。
母亲也是一样,五十多岁就张罗着做棺材。离开老家,跟随我们飘荡的二十多年里,常常会提起她的棺材。父亲在武汉去世的时候,我们在陵园里买了一个双墓穴的墓,其中一个就是给母亲准备的。但母亲总是想着她在老家的棺木,明确地告诉我们,她不想和父亲葬在一起,要回去睡在她的棺木里。还告诉我们,她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要葬的地方。在她清醒的时候,多次强调,她要回去,要葬在她梦见的那个地方。
我来到端头的巷子,母亲果然在那里。双手握着拐棍,两只脚和拐棍组成的三脚架,稳稳地支撑着她的身体,像一组雕塑。我站在她的身后几米远的地方,默默地看着她。
她好像沉醉在那方漆黑的棺木里,世界好宁静。也许,此时才是母亲觉得最安全的时候,她不用漂泊了,不用去那些她根本记不住名字的地方,什么北京,什么武汉,什么唐家,什么高椅,她都记不得,也不想去记住了,因为她根本就记不住。只有这个地方,这方小小的棺木,它不会移动,不会今天在这里,明天在那里。不会让她担心自己丢失在什么自己也说不清楚的地方,丢失在自己无法回家的地方。
我静静地站着,陪伴在母亲的身后。这个时候,我才感到自己是多余的,母亲不需要我陪伴了。她已经有了归宿,她找到了她的归宿。我心里一阵疼痛,好像母亲已经离我而去。眼泪夺眶而出,喉咙里控制不住的声音沉闷而尖利地冲出来,我用手紧紧捂住自己的嘴,但还是惊动了母亲。
她缓慢地转过身,“你什么时候来了?”
(河对岸绿树覆盖的山峦)
我也回过神来,为了不让她看见我的泪眼,我急忙转身看着河对岸的绿树覆盖的山峦。两只正在院子里觅食的麻雀腾空而起,从我们娘儿俩的面前飞过,啾啾啾,箭一样射向屋后山上的树林里。
8.
此时,又是午后。不同的,那天春节刚过几天,是个寒冷而荫蔽的午后;现在,温暖的阳光围绕着我们。母亲还坐在轮椅上沉沉地睡着。
自从母亲拒绝和父亲葬在一起,而且在父亲去世后的这二十多年里一次又一次重申她的主张。我一直想问问原因,几次话到嘴边,终于没能问出口。现在更不可能了,即使问她,她也说不出来了。而且她也不再提这个要求,不是她放弃了,是她忘记了。
母亲大脑已经丧失了界定时空的功能,北京、武汉、唐家村,对她来说已经没有区别,过去她经常会面带惶恐地问,这是哪里,现在已经很少问了。这说明,“哪里”这个概念已经在她的大脑里慢慢消失了。因此,很久没有听见她再提及自己百年后想安葬在哪里。
每次想到安葬,那个问题总会浮现出来,母亲为什么不愿意和父亲葬在一起,仅仅因为眷恋她那口棺材?
我试图回忆起母亲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光,可那已经那么遥远。小时候不明白感情是怎么回事,从来不去考究父母之间的关系。现在想来,唯一印象深刻的是母亲对父亲喋喋不休的抱怨。对母亲的抱怨,父亲总是沉默以对。实在急了,嘟哝一句。因发音含糊,很难听清楚他是辩解还是对抗。除此之外,真的想不起他们之间的更多事情。
看着阳光里熟睡的母亲,我突然有种疏离和陌生的悲凉。这位垂垂老者,随时都可能在沉睡中离我而去,再也不会醒来。而我对她,对她的过去,她的一生又了解多少呢?除了说不清她与父亲之间的故事,她的童年,她的青春,她的心路历程,我又知道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