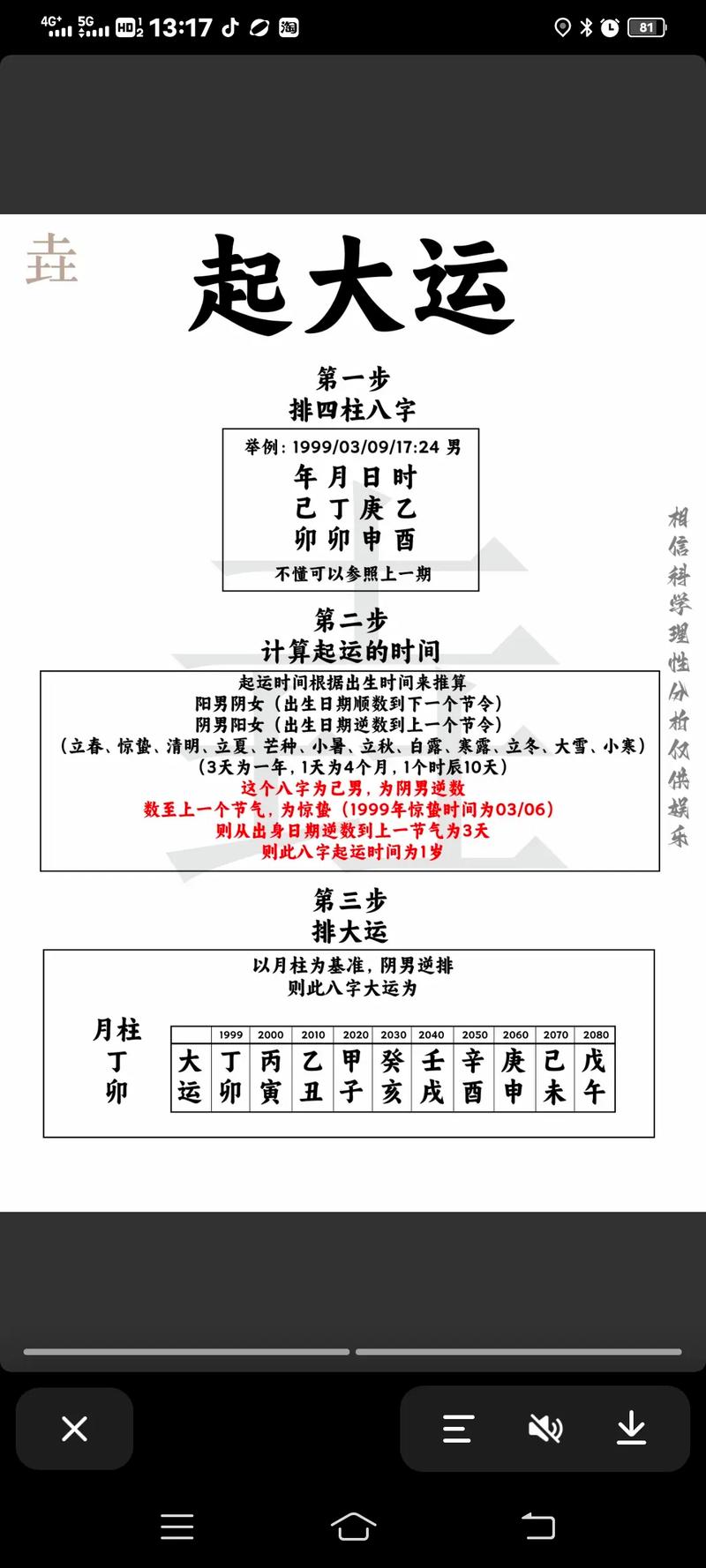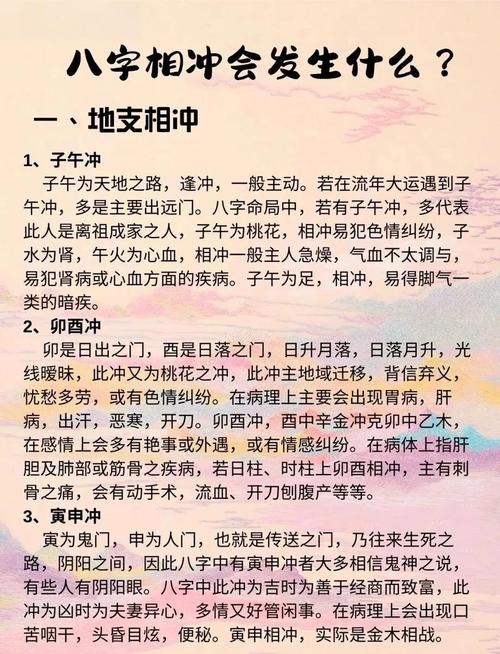大武口文艺【母亲节特刊】|散文《梦里的母亲》作者|杨军民
01
阴历三月十五,母亲永远离开了我。
母亲走得很仓促,凌晨四点突发脑溢血,口吐白沫,人事不醒,中午十二时四十分就没了,没有留下一句话。
母亲这样仓促的离去与她轰轰烈烈的一生极其不符,也与我想象中母亲的故去极其不符。人终要故去,这是不可避免的人生规律,身为人子,当生命到了某一阶段就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不愿想不敢想却又不得不想的问题。我始终认为母亲会被某种病缠倒,我和妹妹萦绕在榻前,端茶送水,买药喂饭,在疼爱和关怀的氛围中,紧紧抓住母亲的手,尽人事而由天命,让她把该说的话说出来,把该流的泪流出来,在亲人的环绕下平静离去。
母亲没让我如愿,她是在睡梦中走的,那是她六十岁生命里唯一的一次懒觉,懒到长眠不醒。
母亲睡觉的那个夜晚,我也睡觉了,我们甚至还通过半个小时的电话,不同的是母亲没有醒,而我醒了。就是这样一个的短暂错位,让我永远失去了母亲。
我是在凌晨五点闻知母亲的凶讯的,哽咽中的妹妹声泪俱下,她只是督促我尽快赶回,或可再见母亲一面。请假、打车、急驰、急驰……车轮在柏油路上翻滚,泪水在脸颊上翻滚。我甚至心存侥幸,母亲会好的,母亲是那么坚强,母亲只是在和我开一个玩笑,她只是在开一个玩笑而已,她会挺过去,大夫会有办法的,现在的医学那么发达。
妹妹的短信接踵而来。
“哥,快回来吧!妈已经被送回了家!”
“哥,快,再让妈见你一面!”
“哥,妈什么都不知道,可当我们在她耳边说你的时候,她的眼角溢出了泪水!”
母亲一生生过六个孩子,独存了我和妹妹。我是母亲唯一可以顶门立户的男丁,此时我却没能守在她的身边。六百公里路程像六百把钢刀刺扎着我的心,我的情绪如奔雷,不停地督促着开车师傅,快,再快些。妻子紧紧地偎依在我身边,劝慰着我,她的脸是一面镜子,从她的脸上看见了和我同样肆意流淌的泪水。
那一刻的阳光绵长无比,那一刻的道路绵长无比,那一刻的思念绵长无比!一车人都沉默着,只听见车子的胶轮在柏油路上淅沥沥响。
好一会儿没响的手机铃声再一次响起,颤抖着手打开,是妹妹的短信:“哥,妈已经走了,注意安全!”手机从我手里滑落,天地昏暗无光,尽量的迈过头,迈过头,把目光抛向车外,泪水纷涌而下,模糊了山川田野。
妻子看见了短信,抽噎着把手搀进我的臂弯,我们簇拥着,任思绪拧成一股绳,甩向故乡。
02
故乡终于近了,习惯地抬头望向村口的那棵老槐树,和槐树下的石碾子,这些极普通的物件,是我和母亲生命的端口。在老槐树下,在石碾子旁,我亲亲的母亲迎我送我。我在她牵挂的目光里远去,又在她期盼的目光中回来。每次转过弯道,母亲总是乐颠颠地跑过来,嘴里一个劲地念叨着:“快,快回家,坐了一路的车,把娃累的。被褥都晒好了,炉子架旺了,炕也烧热了!”母亲瞅瞅这个,摸摸那个,我们相拥着走进村子。
村口没人,老槐树和石碾子孤独的挺立着,一股黏熟的故乡的味道扑面而来。春节走的时候还好好的,怎么就……泪水再一次夺眶而出。
跳下了车冲进屋子,摆设已经发生了变化,原来的家具已被挪开,屋子正中间摆着一张木板床,母亲头朝外静静地躺在上面。母亲穿着一身毛蓝色的老衣,脸上盖着一张纸。床头的一张小桌上点着一盏清油灯,正幽幽的的闪着蓝光。我愣住了,被母亲古怪的打扮和形状吓愣了,那就是疼我、爱我、坚强无比的母亲吗?不,那不是,母亲应该是充满热情和慈爱的!可此刻的母亲冰凉如铁,有一种不可侵犯的抗拒和凛然,卓然决绝的样子。直到族里的一位大婶子一拳擂在我的肩膀上:“瓜娃,咋就不能快点呢!好让你妈见你一面!”大婶的一拳头擂出了我无比的悲痛和眼泪,我匍跪下来,嚎啕大哭,旁边的爸爸、妹妹、妻子和族里的很多妇女哭成了一团。良久,大婶拉一拉我的衣襟:“孩子,哭一哭就行了,你妈殁了,你现在是家里的主心骨。
03
主心骨,主心骨,多年来母亲一直是家里的主心骨,现在母亲走了,我成了家里的主心骨,而我,主持的家里的第一件事竟然是母亲的丧事。
请阴阳、齐家门、借帐篷……一件件事接踵而来,我麻木而机械地应付着。近二十年来,家里难得的热闹,人来人往、熙熙攘攘,花圈林立、挽帐飘展,吹鼓手迈力地吹着,这些悲怆而热闹的仪式是给母亲的,可母亲看得见吗?
后半夜才得片刻消停,为母亲添上清油、续上香,代表母亲生命的清油灯飘忽不定,母亲却躺在局狭的棺材中,大气都不喘一下。静静地看着母亲那张放大了的照片,似乎听见母亲在说:“娃,快睡一会吧,看把娃累得!”我的泪又倏然下来。急切地找来一支笔,想把母亲的功德写下来,把母亲的慈爱写下来,我没有别的特长,只好写一些文字,也算是对母亲唯一的纪念。提起笔,关于母亲的记忆纷涌而来,关怀如海、热语如海、挚爱如海,我却捞不到其中的一滴,任凭那张纸空着、空着。母亲在我的血脉里流淌,我却无法把她分离成文字。为母亲我到底做了点啥,我到底能做啥?我为自己的无能而悲痛欲绝。
母亲丧事正日的那一天,我出门去上厕所,碰见了李婶,李婶说她经常和母亲拉话,在最后的这一段子日子,母亲说她想我,想我媳妇,想孙子,她想孩子们想得睡不着觉!
母亲想我,想得睡不着觉呀!可作为母亲的儿子,我给了母亲什么,总是匆匆来匆匆走,单位没假、工作忙,孩子小等等事由一点一点蚕食着本来应该给母亲的时间。母亲总是把思念藏在心里,说家里好、父亲好她也好,一切都好。这些年家里盖过三次房子、母亲住过多次院,而这一切都是在事后我才知道的。前年冬天,母亲不小心摔伤了脚裸,她用两根树枝当夹板,拖着伤腿照样做家务,照样给乡亲们看病,整整三个月,母亲硬是把我瞒得风雨不透,父亲看不过,要叫我回去,被母亲阻拦了,母亲说娃下岗刚找了个新单位,不要叫娃分心,母亲的心呀,给座金山都不换呀!每次回家知道原委,我都怨母亲,母亲说只要她能动就不会拖累我,除非她被病缠倒了,那真要靠我了。我也暗下决心,等母亲老了真正需要照顾了,我一定一定好照顾母亲,可母亲连这样的机会也不给我呀!
在母亲弥留之际,舅舅满大街跑着帮母亲买衣服,母亲节俭了一辈子,舅舅想让她穿一身好一点的衣服走,可是街上最贵的老衣才二百多块钱一身,舅舅大哭,说母亲辛苦了一辈子,只知道节俭,图个啥呀!
是啊,母亲图个啥呀!
04

母亲的灵柩停放了五天,悲痛的气氛在村庄上空徘徊了五天,母亲的人品甚至被十几公里外的乡亲们传诵着,人们不说母亲的名字,只说某某村看病的那个女人去了。“好人呀,可惜了!”“好积修呀,得了个好快路!”这是听得最多的话。
自母亲去世的那天起,悼念母亲的乡邻就络绎不绝,母亲的好人缘得益于她贤淑的性格和她的职业,母亲当了一辈子赤脚医生,人又极善良,她以一个医者的身份在乡村奔走了一辈子,接生过无数孩子,送走过无数老人,母亲没有得到过一张奖状,可她的功德在乡亲们的心里。农村妇女悼念亡者的形式很质朴,进门不说一句话,点纸上香后就号啕大哭,如丧家兄般号啕大哭,有两个居然昏厥了过去。母亲去世的那天,一个邻居的婶子还在等母亲为她输液,当她等来的是奄奄一息的被人抬回来的母亲时,本来就有心脏病的她,因为接受不了现实,躲开了母亲的丧事。可在起灵的那一天,婶子忽然跪在棺木前大哭,她让母亲原谅她,她觉得她应该在母亲最后的时间守在母亲的身边,她却走了,她觉得她对不起母亲,她让母亲千万要原谅她,原谅她。
05
出殡那天,我早早的来到墓地为母亲扫墓,在山上,那块被母亲耕作了一生的土地上,墓穴像一个张着血盆大口的怪物,等着吞噬母亲。我钻进墓道,为母亲点上长命灯,献上供品,仔细地扫着本来就洁净无比的黄土,这是母亲的新家。阴阳先生抓起一把黄土称赞着它的酥软,称赞着墓穴的风水,我却感到了局狭和潮湿,母亲就要在这么小、这么阴暗的地下躺着了。母亲的一生盖过三次房子,在我刚工作的时候还为我买了房子,最终却不能住在自己的房子里。
就是在去年的九月,母亲还满怀信心地盖房子,母亲用一生的积蓄在家里原有的平板房上摞了二层,母亲说她和父亲老了,房子可以出租,可以为他们挣来一些养老费。母亲的这一举动是为了回应我和妻子之一再让她和父亲去我家住的行动证明,母亲说只要还能动她就不给孩子添拖累。房子盖好了,母亲把二楼铺上了地砖,置办了新里新面的被褥和床,那些是母亲为我和妻子准备的,母亲说我妻子是城里人,爱干净。我和妻子每年住在家里的日子总共不到10天,母亲就让房子那么空着。我劝母亲住进去,住一住干干净净的新房子,母亲执意不肯。后来劝多了,她说等到夏天,她到里面凉凉的住几天。可是没到夏天她却没了,母亲没在二楼住过一天呀!母亲呀,家里的房子空着,空着呀,你却为什么要躺在这么潮湿的地下。如果,如果知道是这个结局,我倒宁可您把房子盖到地下,那样你就可以躺在窗明几净的房子里了。
为母亲的棺木撒下第一把黄土后,乡亲就把土流水般撒下去,母亲在那一锹锹黄土里,在我蜂拥的泪水和不断续着的白纸和黄裱的火焰里渐渐远去,以致最后成为一个新鲜的坟丘。
乡亲们完成任务般撤退了,我匍跪在新坟前,把脸贴在新土上,我想知道母亲在里面好不好,憋屈不憋屈,却听见母亲说:“娃,快回去吧,人都走完了,山上荒的!”
母亲呀,是呀,山上荒的,我们都走了,你怎么办呀?
06
答谢了总管、阴阳和乡亲,我和父亲、妹妹又把家里的摆设恢复了原状,一切都按母亲生前的样子摆的,父亲说那样他会好受一点,他可以迷惑自己,认为母亲是去走亲戚了。
父亲开始铺床,把他与母亲的那张床铺得平平展展,又把我们的床铺得平平展展,然后说在七天之内母亲的亡灵会在家里,她兴许会托梦,如果托了一定要告诉他。母亲是到妹妹家窜门的时候发的病,听了一辈子安排的父亲想听母亲最后一次安排呀!
那一晚,我真梦见了母亲,母亲在外公家的老窑洞中,那里有亡故的外公和外婆,母亲黄着一张脸,怯怯的样子,一句话也不说,也许在那个世界里母亲还很陌生。
第二日,妹妹来电话说她也梦见了母亲,具体情节记不住,反正梦见了。
一个婶子来探望父亲,说她也梦见了母亲,母亲在那个世界里还是开诊所,不过那个诊所又宽敞又敞亮,可不像我家的又黑又旧。
那一刻,我看见父亲面色苍白,拿着烟的手在颤抖。
为母亲挂完灯,过了头七,我准备返回单位,临走去父亲的屋里道别,见父亲捧着母亲的照片,泪流满面喃喃自语:“花,你给孩子们都托梦,咋就不给我托呢,我知道我没本事,你嫁给我委屈了,我知道我老跟你生气、骂你,你记恨我,那你托梦骂我也行呀!我就是想知道你临走想说些啥!”
悲痛又一次涌上心头。
母亲,你就给父亲托个梦吧,你的生命之门已关闭,但我们的梦是为你敞开的,我们还没有听够你的安排和关爱呀!
父亲想你,我们也想你呀!
大武口文艺公众平台
往期回顾
01
02
03
长按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