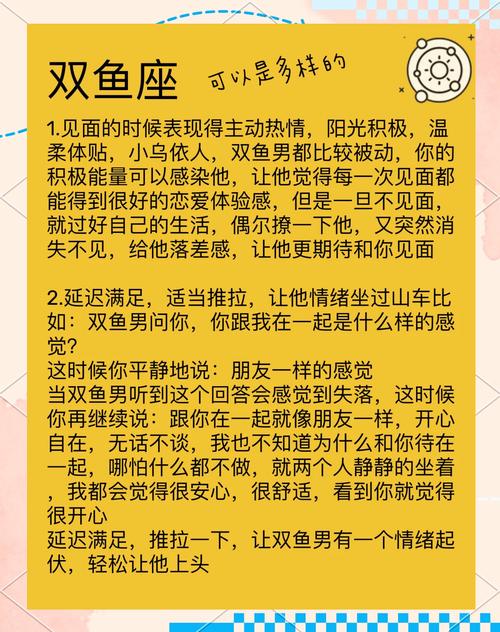裘山山|短篇小说:腊八粥
腊八粥
□ 裘山山
(原载《文学界》2008年第3期)
赵清雅走进营业厅,取了一个号,就坐到大厅的长椅上等候。号是59,下面写着:您的前面还有7位客人。7位不应该等太久吧?她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眼睛实在是太涩了,涩得想流泪。她知道这是连续三天失眠的后果,她还知道此时若有面镜子的话,一定能映出一张菜黄憔悴的脸。年过四十后,她本无好脸色了,还长期失眠,还连续遭遇打击,母亲去世,鲁可失踪。雪上加霜啊,屋漏偏逢连阴雨啊。不过她已经无暇关心她的脸色了,她甚至很少照镜子。照镜子是需要心情的,她每天早上躺在床上,除了头昏还是头昏,除了沮丧还是沮丧。勉强爬起来穿上衣服,对付几口早饭,怎么都想不出一件她有兴趣做的事。鲁可在的话,她至少要带它下楼走走,给它擦擦蹄子,弄点儿吃的,再抱着它说两句话。如今这世界连狗都不需要她了。今天凌晨她刚有点儿迷糊就做恶梦了,梦见鲁可跳上床打滚儿,还把头往她手心里拱。它最喜欢这样撒娇了,要主人摸它的脑袋。她刚摸两下,手心儿忽然冰凉,鲁可就僵硬在那里,变成一条死狗了。她一惊,就清醒过来,醒过来手心居然有冷汗。鲁可原是她生活中唯一的光亮,唯一的温暖,却在三天前突然消失了。尽管她坚决不相信它遭遇了不测,但种种迹象都表明它的确是遭遇了不测。她每天坐在家里发傻,竖着耳朵听那些细微的响声,害怕错过鲁可跑进门时悦耳的蹄声。欲哭无泪这个词也不知是谁创造的,概括了多少悲伤和哀恸啊。她的失眠症因此而加重,从每天夜里只睡两三个小时,加剧到只睡两三分钟,甚至一分钟没有,她总是醒着痛着,躺得一身骨头都是疼的,没有一个姿势是舒服的。她曾试着横过来睡,把身体的南北走向改成东西走向,也不行;又抱着被子到客厅的沙发上去睡,还是不行。她还到母亲的床上去试过,哪怕能睡着一小会儿也行啊,可更不行了。在无法入眠的漫漫长夜里,在翻来覆去的折腾中,她把自己一生的不幸都翻检出来了,反复折磨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她的心稀烂,如绵绵淫雨后的郊外小路。她就在那样糟糕的心境中漂浮着,清醒的漂浮着,简直要崩溃了。有几次她爬起来站到窗前,望着窗下密密麻麻的房子发呆,她的公寓在28楼,她羡慕那些住在又低又矮又小的房子里酣睡的人们,她渴望加入那个酣睡集体,在无知无觉中沉下去,沉到最底层,恍惚中她觉得自己已经一跃而下了……
在无法忍受的那个早上她去看医生,脸庞瘦削、目光冷峻的医生听完她的讲述后竟单刀直入的问,你是不是想死?她条件反射的答到:没有啊!我没有想死啊!好像在抵赖一次犯罪念头。医生嘴角有一丝冷笑,说,你刚才说了两次,活着真没意思。活着真痛苦。这难道不是想死吗?她愣在那里。这话好像是她说的,但活着痛苦和想死,似乎还不是一回事吧?医生给她开了药,据说是进口的,价格昂贵。但她吃下去后依然睡不着,反而更难受了,心里扑腾搅和,一刻也不得安宁。一种折磨衍生出两种折磨。她只好停下药,继续忍受着清醒的煎熬。她从不跟人诉说,自己关自己的监狱。后来报纸送来了,她在社会版上看到一条消息,当地一个女人,自己花钱在乡下买了个院子,收养了很多流浪狗。她连忙打电话过去询问,当然没有她的鲁可,但毕竟,她想到了一件她可以做的事。于是草草洗漱出门,开车到银行。
赵清雅闭着眼,耳朵却张开着,怕叫过了自己的号。忽然有人轻轻拍她,她睁开眼,一瞬间感觉到了自己眼袋的重量,那里面拖载着无数个不眠之夜。沉重的眼袋前,是一张年迈女人的脸,简单的说是一张老婆婆的脸,比她过世的母亲更加苍老。那脸与她只有几公分的距离,以至于她嗅到了她的口臭。老婆婆轻声说,小妹儿,麻烦你帮我个忙嘛。赵清雅愣在那里。一来她竟然叫自己小妹儿,二来,她已经很久没有这么近距离的看一张脸了,而且是笑脸。因为惊诧,她半天没应出话来。老婆婆索性坐到她身边,更加小声的说,就一点点小事情,一下下就好了。赵清雅还是愣着。老婆婆费力的解开自己上衣的第二颗扣子,又解开里面夹袄的扣子,指着怀里说,你帮我把里面口袋上的别针取下来好不好?我自己随便怎么都解不开。老婆婆做这些时,赵清雅再次惊住,那是一双什么样的手啊,几根指头都变了形,弯曲着,干裂粗糙,用个不好听的形容,如鸡爪一般。老婆婆看出她的吃惊,笑眯眯的说,我有痛风,老毛病了。老婆婆穿着件紫红色的防寒服,是早些年的样式,领子油乎乎的,显然从穿上就没洗过。防寒服里面是一件更旧更脏的夹袄。赵清雅略微有些犹豫,倒不是嫌她脏,而是她已经很久没和人这么近距离接触了。但她无法拒绝帮她这个忙。她只好将手伸进老婆婆的夹袄里,果然摸到一个别针,可一只手还无法打开,她只好再凑近些,用两只手去解。两张脸那么近距离的挨着,让她有些别扭。这辈子除了母亲,她没跟谁凑这么近过。赵清雅摸索着,终于将别针打开了,拿出来递给老婆婆。老婆婆高兴的说,噢,太好了。又说,你再帮我把里面的存折拿出来嘛。赵清雅又伸手进去,在别针别住的那个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存折。存折一看就很有些年头了,四周的边儿都磨损了。老婆婆宝贝似的接过来,放在手心里,再用另一只手的拇指摁住。她的右手拇指好像不能用了。她满面笑容的说,谢谢了谢谢了!然后颤巍巍的朝柜台走去。赵清雅想,这是谁家的婆婆啊?难道是孤寡老人?
这时扩音器里叫到了59号。赵清雅站起来去办她的业务。银行小姐问她,全都取吗?她点头。小姐说,我们最近推出一种新的理财产品,你要不要看一下?非常合算的,年收益最低都可以达到10%以上,时间也不长。边说边递给她几份花花绿绿的资料。赵清雅用手推开,摇头。小姐不再说什么了,给她办理。这让赵清雅很感激。有几次遇上很执著的,没完没了的动员她,让她难受。她不想跟人说话,费口舌。赵清雅把取出的钱一捆捆丢进随身带的大包里,拉上拉链,提起来时发现挺沉。钱还是蛮有分量的。她起身回头,发现刚才那个老婆婆竟然还没走,好像等她似的。老婆婆站在那儿,头上是一顶姜黄色的毛线帽,身上是紫红色色的防寒服,袖子上套着深蓝色的袖套,脖子上围着一条杂色的彩条围巾,胸前还挂着一双军绿色的棉手套。那么多颜色集中在她矮小的身上,让她看上去像一块调色板。老婆婆冲她一笑,熟人似的。小妹儿。她还是这么叫她:小妹儿,你再帮我个忙嘛,帮我把这个放回去嘛。老婆婆从手套里取出手,手上捏着存折和钱。赵清雅点点头,接过来存折和钱,钱不会超过500,帮她塞进怀里的口袋里,再用别针别上。因为取过一次,已经熟悉了,所以很快就做好了。做好后赵清雅说,你回去拿不出来怎么办?说这句话时赵清雅忽然意识到,这是她许多天来第一次开口说话,声音有些粘住了。老婆婆说,不会的,回去了我就把衣服脱下来慢慢取。赵清雅想,噢,我真够笨的。老婆婆摁摁胸口,感觉到了钱和存折的硬度,放心了。她很贴心的跟赵清雅说,这是我的生活费,我每个月都可以取那么多呢,用不完呢。赵清雅笑笑,没有说话。老婆婆说,你不要看我这个样子,其实生活上我不从来不心焦。踏实得很。赵清雅帮她拉开银行大门,让她走出去。老婆婆走出门,站在那里警觉的四下打望,没有迈步。赵清雅下了两级台阶,回头看她还站着,就说,婆婆,要不我送你回去吧,我有车。老婆婆喜出望外,哦哟,我今天运气好好哦,简直有菩萨保佑哦。
赵清雅带着婆婆走到自己车旁,开门让她坐上去。她让她坐在后面,替她关上门。老婆婆靠在椅背上连连说,好巴适噢(四川话,舒服的意思),好巴适噢!赵清雅没有说话,打开车上的热气。然后问她,你住哪儿?老婆婆说,没有好远的路,就在太平洋大厦背后。你过去我指给你看嘛。老婆婆又说,你这个出租车好,比街上的出租车好。我坐过出租车的。赵清雅有些想笑。没想到老婆婆把小车都看作出租车。
天还是阴的,似雨非雨。车子已经很脏了,档风玻璃上斑斑驳驳的,只有中间雨刮器扫到的半圆是亮的。她一直懒得去洗。这两个多月来她如同行尸走肉,哪有心情洗车?母亲的去世对她打击太大了,其实母亲在世时她也常和母亲发生冲突,两个单身女人,各有各的毛病。但母亲毕竟是这个世界上她唯一的亲人,甚至母亲就是她生活的一部分,身体的一部分。母亲在的时候,母亲,她,还有鲁可,三位一体,很完整。她们每天一起吃饭,一起散步,一起看电视,有时甚至挤在一起睡觉。母亲去世后,鲁可只陪了她两晚上就消失了,好像被母亲带走了似的,空空的大床冷得像冰湖,让她无法站稳,无法安宁。她知道鲁可很悲伤,比她还要悲伤,只是无从表达。从鲁可到这个家后,10年来没有离开过母亲半步,母亲给它喂食,给它洗澡,给它梳理发毛,给它发炎的耳朵点药,甚至给它挠痒痒。她们才是真的相依为命。鲁可因此而自寻短见,赵清雅一点儿也不会奇怪。可她还是嫉妒母亲,她到另一个世界也有伴儿了,她却如此孤单。这两个月她生不如死,生活中一丝热气儿也没有。而作为这一切悲伤的背景,是持续两个月的阴天,周遭阴冷寒彻。她都奇怪自己还活着,没有被心痛痛死,没有被绝望杀死。
老婆婆说,小妹儿你是做啥子的?赵清雅不想回答,假装没听见。老婆婆说,我晓得你是做啥子的,我看的出来,你是干部,政府的干部,对不对?赵清雅还是没吭声。老婆婆又说,你有点儿像我们街道上的邱书记,多合适的,斯斯文文的,不过呢,邱书记很爱笑,说话声音多大。每年过年她都领起街道上的人来看我,还送东西,一桶油,一袋米,有一回还送了新衣服的。我是孤寡老人的嘛。我老头子走了十年了,我们又没有娃娃。所以是孤寡,政府要慰问。我们街道上连带我有7个孤寡老人的嘛,邱书记说道,全部是婆婆,一个大爷都没有。好好笑哦。晓得咋搞的哦,我们婆婆些好经活哟!
老婆婆自己说着自己笑起来。赵清雅只是噢噢的应着她,还是提不起说话的热情,任老婆婆的絮叨在车里盘旋。赵清雅早已与谈笑风生绝缘了。这十几年来,她的日子一直是黯淡的。就是再往前推,她也从没放过什么光彩。父母在她1岁时离婚了,她没有兄弟姐妹,也没有继父,甚至没有姨妈舅舅。更重要的是,她也没有丈夫。她的耳朵从小灌满了母亲对男人的憎恨,令她对婚姻充满恐惧。一直到33岁,好不容易克服恐惧准备结婚了,手续都办好了,请柬都发了,丈夫却在婚礼前猝死,脑血管破裂,少见的病。这让她很受刺激,认定自己是不适合婚姻的。任期短暂的丈夫,却给她留下了一笔存款和房子,使她和母亲足以安稳度日。可两个婚姻不幸的女人在一起,能快乐吗?母亲今年才71,算走得早的。即使如此,赵清雅想到自己还要熬到母亲那个年龄,差不多三十年,心里就发怵。这可怎么熬啊。

老婆婆忽然说,到了,就是前面杂货铺旁边那个院子。啊呀,这才快当呢,一下下就到了。好巴适哦!你不晓我今天早上走了好久,我吃过早饭就开走,走拢银行都开门了,都有好多人排队了。要不是遇到你,我起码要吃午饭才能走拢屋,揣起钱又还不安全。你简直是活菩萨哦,好人哦。赵清雅忽然打了个哈欠,老婆婆的絮叨让她脑袋有些发懵了。她开车进院子,发现院子还不小。她停车开门,扶老婆婆下车,立即引来一些人的目光。有人说,耶,周婆婆,你今天耍洋盘了嗖?老婆婆说笑眯眯的说,就是,人家小妹送我回来的,人家小妹多好的!赵清雅有些不好意思,老婆婆当着大家叫她小妹。虽然她的身材依然保持着做姑娘时的样子,可她那一脸的沧桑和青黄,谁都能看出真实的年龄,除了老婆婆混沌的眼睛。老婆婆回身拉住她说:到我屋里坐一哈儿嘛,就坐一哈哈儿。赵清雅不想去,正迟疑着,忽见一只脏乎乎的小狗奔跑而来,冲到老婆婆跟前热烈的扑腾,后腿直立,前爪张开着像孩子似的要抱,跟鲁可真像啊。赵清雅忍不住蹲下身去说,哦,乖乖!小狗立马回过头来扑她,熟人似的使劲儿摇尾巴。赵清雅伸手去摸它的头,它却一下子闪开了。赵清雅想了想,将自己的包锁到车的后备箱,然后随着狗狗走过去。
院子里有几栋老砖楼。老婆婆却走到背对楼房的角落,打开一间紧靠围墙的小偏屋,那小偏屋最多两米高,泥墙木门。老婆婆回头招呼她,来嘛,进来坐嘛。赵清雅有些发傻,她从来不知道城市里还有这样的住房。屋子是长条形的,宽两米长三米的样子,只有她家厨房那么大。靠门摆了一张床,挂着发黄的蚊帐,蚊帐前面的横粱上,挂着几件洗了的衣服。床里面一个旧的双门木柜,床对面是一张现在很少见到的木桌,桌子下面堆满了乱七八糟的旧纸箱,旁边一个长条凳,凳子上也堆着杂物。屋子角落还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满腾腾的,乱麻麻的,又黑又阴冷。赵清雅觉得哪里像住人的地方啊,就是个破仓库嘛。她问,你一个人吗?老婆婆说,我和乖乖两个。赵清雅说,乖乖是哪个?老婆婆笑道,狗狗。哦,赵清雅明白了,难怪刚才自己一说乖乖,狗狗就跟她亲起来。老婆婆说,我们老头子原来是这里看门的,那个门房拆了,我不想走,就在这儿将就盖了个屋。赵清雅说,那大爷的单位上没没给你解决房子啊?老婆婆说,解决喽,好远哦,二环路那边去了,我不想去。还要交8大8万块钱,我哪儿有那个钱哦,我就拿给侄儿子了,我侄儿子还补了我1万块钱呢。赵清雅说,那你也不合算啊,现在房子好值钱哦。老婆婆说,啥子合不合算哦,我还活几年哦。我还是住到这儿安逸,啥子都方便。
老婆婆动作很大的扒拉开床上的衣物,让赵清雅坐床。赵清雅看看再无地方可坐了,只好坐下去。回头看,狗狗正很乖的趴在门口看她,也没跟进屋子乱闹,这点比鲁可好多了,若是鲁可,早就跟着跳上床趴她腿上耍赖了。赵清雅一坐下就感觉屁股下面又凉又硬,用手一摸,床上就铺了一床跟纸板似的旧棉胎。再看被子,也是薄薄的一床,破旧不堪,似有股霉味儿,这小屋显然是晒不到太阳的,更何况太阳已经很久不见了。赵清雅有些心惊:婆婆,你垫这么少,盖这么少,晚上不冷吗?老婆婆说,不冷不冷,我在上面搭了棉衣的,还有这些。老婆婆指指她推开的那一堆东西,原来那些乱七八糟的衣物,是用来晚上搭在被子上的。赵清雅顿时有些辛酸,她脑子里闪出个念头,去给婆婆买床新被子吧?对面就是大商场。现在一床被子能花多少钱啊。老婆婆一个月三五百块生活费,肯定是舍不得买的。
小屋外面还有间更小的屋,算是厨房。老婆婆走进去,乖乖也忙不迭的跟进去,老婆婆喝了一声,它又老老实实出来了。赵清雅说,它是不是饿了?老婆婆说,莫管它。她倒了杯水递给赵清雅。赵清雅端在手上没有喝。老婆婆连连催促:你喝嘛,喝嘛。赵清雅没办法,只好喝了一口。老婆婆盯着她问:甜不甜?她说,甜。老婆婆说,不甜我再给你加点儿,院子里的赵婆婆拿给我的蜂糖,好大一瓶哦。她连连说不用了够甜了。老婆婆说,你气色不好,吃点儿蜂糖就好了。赵清雅说,婆婆你床上太单薄了,我去给你买一床铺盖吧。老婆婆说,不消不消(不用),我有新被子,我有好多新被子。不消买。你看嘛。老婆婆拉着赵清雅进屋指给她看,在蚊帐顶上的房粱下面,搭着一块木板,木板上有好几个大编织袋。老婆婆说,那里面全是我的新被子,有街道上送的,还有老头子原来单位上送的,每年冬天都送,送温暖的嘛。赵清雅说,那你为什么不拿来用?老婆婆说,旧的还没用烂嘛。赵清雅说,你那个还算不烂啊?很烂了,可以扔了。你不用这些新的省给谁用啊?老婆婆仰头看了一下房粱上的那堆东西,笑眯眯的说,你说的也对哈,那就用嘛。你帮我拿一下嘛。
赵清雅踩到长凳上,够不着,只好拉过桌子,重上凳子,再爬上去,这才能够着,也不知是谁帮婆婆放上去的。她连拉带拽,弄下两个编织袋来。打开一看,可不是,一床弹花被,一床太空棉被,还有被套枕套,都簇新簇新的。她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床上那些烂棉絮脏被子包括又硬又脏的枕头卷起来,扔到外面。再打开包装袋,把厚点儿的弹花被铺到床上当褥子,再把软和些的两床套上被套做铺盖,就是没枕头,她想了想,把一床毛巾被叠好塞进枕套,再铺上新床单,一张床顿时焕然一新了。
赵清雅竟然忙出汗来,她脱掉呢子大衣,将一地的包装袋什么的归置起来,抱出去扔。走出门,见老婆婆不知在厨房忙乎什么,喊了两声也未喊应,只有热气从小窗户逸出来。赵清雅觉得很累,就一屁股坐在了床上,一眼看见乖乖趴在她扔出去的旧棉絮上,很舒坦的样子。下巴搁在前爪上,愣愣的看着她,眼里有她熟悉的忧郁的眼色。狗狗的眼神总是那么忧郁。她拍拍床,示意它过来。它没动。若是鲁可,有人这么动床早就闹翻了。她忽然起了个念头,自己可以再养一个狗狗的。一个哈欠不期而至,赵清雅一歪身子靠到被子上。新被子的味道进入了她的鼻孔,久违的倦意忽然袭来,她又连连打了几个哈欠,眼泪都出来了。她想跟老婆婆打个招呼,赶紧回家去,却不知怎么,一头倒在床上,睡着了。
她睡啊睡啊,好像睡了一辈子那么长。起初她还隐约听见声音,有人在聊天,有人在说笑,孩子的打闹,婴儿的啼哭,鸟儿的叽叽喳喳,溪水流过,风吹树梢,安静村庄里的狗吠,早晨的鸡鸣,小巷里的吆喝,学校里的琅琅读书声……所有她听到过的好听的声音,都一一出现了。后来她听见有人在唱歌,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这些都是母亲爱唱的歌了。歌声时远时近,时大时小,却始终环绕着她。她终于在歌声里放松下来,松得像新棉絮一般,软软的,暄腾腾的,再后来她就失去意识了,睡了过去,睡得很沉很沉,一直沉入万丈深渊,沉入海底,变成了一粒细沙……
醒来时,赵清雅不知身在何处。睁开眼,老婆婆正凑得很近很近在看她:你醒了哇小妹?你终于醒了!你睡了好久哦。你再不醒来,我就要去喊二单元的王医生了。你没的事嘛?赵清雅摇摇头。老婆婆松口气,高声亮嗓的说,哎哟简直把你给累到了。开出租车送我回来,又帮我整床,简直把你给累到了。我看你睡得好香哦。肯定是累到了。昨天晚饭都没吃,我喊你喊不醒呢。赵清雅神思恍惚,全身却轻松暖和,仿佛还阳一般。她已经太久太久没有这样睡过觉了,太久太久没有无知无觉一小时以上了。她想,自己大概睡了好几个小时吧,一看表,天哪,岂止是几个小时,此刻已是上午11点了!也就是说,她从头天中午一直睡到现在,睡了12个小时!真是奇迹啊。她坐起来,发现门缝里有阳光泻入,自己身上盖着新被子,鞋也脱了,跟着,她看到了乖乖,趴在她的脚跟旁边,比她睡得还香。而老婆婆却如昨天一样穿着那件紫色的防寒服。她马上翻身坐起,连连说,婆婆太不好意思了,我都不知道我怎么睡着了。老婆婆说,有啥子不好意思哦,你帮我那么多,我拿啥子还你嘛。睡个瞌睡有啥子嘛,你这种贵人我请还请不来呢。赵清雅说,那你昨晚不是没睡成?老婆婆说,我还是趴到床边打了瞌睡的,莫来头。人老了瞌睡少。你看乖乖和你一起睡的,它喜欢你哦。
老婆婆拉开门出去了,阳光倾泻而入,小屋顿时亮堂起来。赵清雅完全清醒了,却有些不知所措。这时老婆婆从厨房端了碗热腾腾的稀饭进来,递到赵清雅的手上:你晓得不,今天是腊八,我早上起来就熬了腊八粥,香得很,你赶快吃一碗,肯定饿惨了。我还有泡菜,我的泡菜之巴适,好多人都找我要。我给你装了一瓶,等会儿你带回去下饭。
赵清雅端着热腾腾的腊八粥,任热气一阵阵的飘拂在脸上,半天也没动口。她忽然放下碗,一把抱住了老婆婆。老婆婆那么矮小,她要弯下腰才能抱住她。她把她的眼泪,蹭在老婆婆那件油乎乎的防寒服上,眼泪越蹭越多,让她抬不起头来。老婆婆用几根手指轻轻的拍她背:吃饭,小妹儿,吃饭,刚熬好的腊八粥,多巴适的,我是用了心的,花生核桃莲子芝麻,还有红枣,啥子都请齐了,吃了身上肯定热热乎乎的,又还营养。
(原载《文学界》2008年第3期,《小说月报》2008年第5期选载,获第十三届小说月报百花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