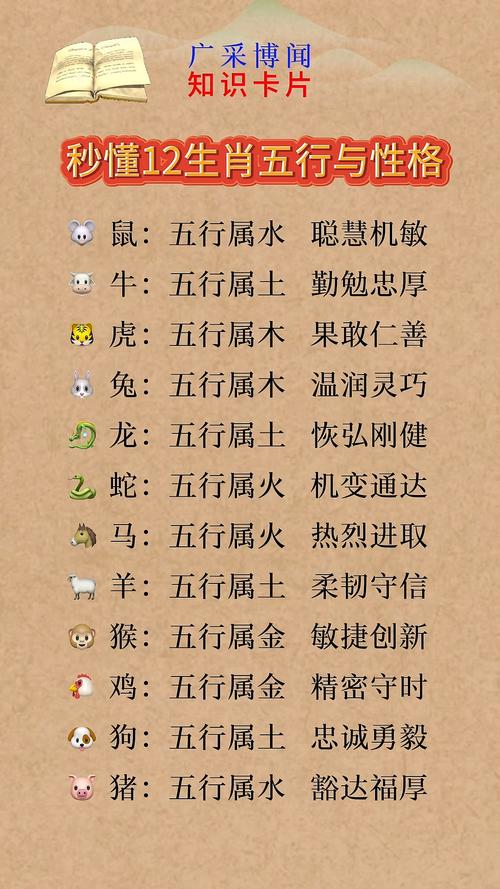老屋,时光里的嘘叹 ▌姜 峰
01
父亲说,好久没回家了,想回家看看。
我随父回家,走在路上,父亲步履雄健,脸上红润。我心想,父亲八十岁了,身体还挺好。到家了,过第一道门,正厅,过天井,至第二个正厅,再是天井,至最里面厢房,见母亲坐老式雕花床上。心想,母亲出远门很多年了,今年也回来了,真好!
我忙喊:妈妈、妈妈!她不答。
突然意识到,母亲过世多年,怎么又回来了?我连忙大喊:妈妈,妈妈!她不答,转身往里走,往那幽深幽深老屋走。我急了,妈妈,妈妈!一直大喊。
妻推醒我。原来是南柯一梦。
想着,母已逝三十多年,每次梦见,都是出远门很久很久,然后回家了。父跟我们在长沙生活二十多年,在八十岁那年去世,也已经走了四年。几次梦见,父总说想回老家看看。
今年清明节,因为疫情,没能回老家给父母扫墓,却做了这样一个梦。
很奇怪,常在这样的日子,清明、七月半,或者父母生日前,梦见亲人,梦见老屋。
灵魂深处,特殊的日子,亲人总在提醒。
梦里,总是在老屋,这个我十四岁前住居过的地方,如今,早已踪迹全无。
儿时生活的地方,却总是静静地徜徉在时光的隧道里。
02
老屋所在的村,在一高坡上,两棵古老的樟树,矗立于村口,坡下是辽阔的盆地。
金黄的稻谷,田田的莲叶,静静的村舍,依次在视野打开;远处黄材镇、青羊湖大坝、千金坪山等,一览无余。
滔滔沩水,从千金坪山脚从西往东流向远方。
老屋建筑座北朝南。
村口第一道大门,称槽门。斑驳的旧门楼,年代久远,小黑瓦,陈旧的门框,槽门东留下一段残垣断壁,爬满枝叶茂盛不知名的藤,结出一种绿色的圆圆的可以吃的果实,小时叫它“棒棒”,至今我不知其学名。
过槽门,是一大坪,西头水泥坪,生产队晒谷坪,坪最西边为生产队队屋。
大坪东,长长石板路,二十多米,由南往北,通往第二道槽门。门框和门槛麻石砌成,两边各有一竖立的石鼓,被摸得闪光发亮,石门槛也被我们坐得锃光瓦亮。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那个人民公社的饥荒年代,单瘦单瘦的弟弟,常坐石门槛上,盼父母收工回。邻居龙大哥生产队收工回,问弟:“恰饭冇?”弟答:“恰了。”“恰么业?”“恰汤。”不管吃没吃饭,弟都答“恰汤”。长大后,一直被龙大哥作笑话讲。
大门两边是厢房,正面露天天井,天井东西两边是堂屋,连着厢房,天井北为正厅,实为公共场所,家族祭奠和活动的地方,也是我们儿时玩耍之处。此为老屋第一个四合院。
从正厅后门,进入第二个四合院,结构如前。从第一个四合院,从南往北,分别住着我大伯、二伯、三伯家,我父母及祖母住第二个四合院最北边。每家三到四间房子,加上共用的堂屋,杂屋,大大小小加起来有近二十间房子。
紧邻我们的有龙家、另外一家姜姓的几个四合院,这些,一起构成了这个老村的结构。
03
老屋厢房,有一间肯定是姑妈住过的。姑妈做闺女时的故事是在她逝后才听到。
八十多岁的姑妈病逝。我到姑妈家吊唁后,当晚,住堂兄家,一位远房长辈亲戚也住这。他对我说:其实你姑妈的大儿子不是这姑父的,你姑父追你姑妈的故事很有传奇性。
姑妈之前还结过一次婚吗?我一直不知道啊!很奇怪,怎么没听父亲说过呢。
远房亲戚说:也许你父亲并不知晓,那时你父亲还小呢。
父亲是家中幼子,上面还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其二姐岀嫁不久就病逝,自然我没见过;姑妈,是父亲大姐,比父亲大了十八岁。
远房亲戚说:你姑妈是长女,也是你祖父的掌上明珠,到了岀嫁年龄,高不成,低不就。当时,在你祖父家做长工的周家小伙,暗暗喜欢你姑妈,担心你祖父不同意,也不敢提出来。那一年,来了一支部队,住厉家祠堂,有个军人看上了你姑妈,他姓贺,家里就是邻村的,委托其父母来提亲。
祖父时,家里并没有自己的田土,只是承包了厉家祠堂的几十亩水田,上交租金给厉家祠堂,每年负责厉家的祭奠活动,只能算是厉家祠堂的佃户。几十亩田,平时请了两个长工,农忙时节还要请短工。祖父善于经营,勤俭持家,所以家境还算过得去。
祖父打听到,贺是读书去长沙的,抗日战争爆发后,投笔从戎,是一上进青年。于是,同意了这门亲事。
姑妈结婚时,我父亲还只有三岁,锣鼓唢呐,大红轿进门,热热闹闹,最高兴的是我父亲,他钻进大姐的大红轿里不肯下来,一起抬到了贺家。这事一直被作为我父亲小时候的笑话,被人提起,直到他结婚后才很少人说。
新婚后,丈夫去了长沙,姑妈大多时间住娘家,一年后,生下一儿子,这就是我的大表哥,只比我父亲小四岁。
1944年初,姑妈丈夫回来一次,多住了几天,临走时依依不舍,说又要打仗了。
长沙战事吃紧,姑妈丈夫却杳无音信。
年底,乡公所送来通知,说贺连长在长沙保卫战中牺牲,也有人说是在宁乡牺牲的。
姑妈带着幼小的儿子,住在娘家,常常暗自流泪。
周家小伙一直暗恋着姑妈,默默照顾着。
1945年秋天,是一个丰收年,稻子收割时节,家里多请了几个短工。祖父习惯于早起,看看哪丘田里的稻子熟了没有,是否可以收割了。
这天凌晨还没起床,就听到外面吵吵嚷嚷的,走出一看,只见周家小伙被同伴五花大绑。伙计说,周家小伙昨晚在姑妈房子里过夜。
祖父操起身边的扁担就要打,这时,姑妈从房子里面跑出来,挡在了前面,跪在自己父亲面前:“要打,您先打我吧!除了他,我谁也不嫁!”
见生米煮成熟饭,无奈,祖父同意了这门婚事。
后来知道,其实,周家小伙并没有做这出格的事,都是这帮同伙替他出了这么个馊主意。
在我印象中,我的姑父,一直对姑妈很好,家里大小事都是姑妈管事,姑父只管做体力活,姑父尽管年龄比姑妈大,但身体结实,八十多岁还能做农活,还能挑一百多斤的担子。姑妈晚年眼睛不好,后来瘫痪了几年,都是姑父细心照顾。姑父到九十八高龄过世。
不知姑妈当年嫁贺家,是否愿意,是否幸福,那是一段短暂婚姻。
也许人生姻缘上天注定,缘由天定,份属人为,天给机会,人做抉择。后来姑妈嫁周家小伙是自愿的,一生是幸福的,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
04
梦里总少不了老屋的雕花床。床前面是踏板,两端放床头柜,床架是双层镂空雕花,两边各有一只蹲着的小狮子,栩栩如生。小时在床边蹦蹦跳跳,最喜欢摸着狮子头玩,狮子头被我和弟弟妹妹摸得光溜溜的了。床前上面的雕花物有花有鸟,往外伸岀三层,一直伸出到踏板外面。后来,床上面的雕花雕像慢慢往下掉,只剩下里面一层。
印象中,几个伯父家都没有雕花床。雕花床应该是祖父母留给父亲的。
祖父过世时,父亲尚只十六岁。家里的主心骨没有了,大家庭分崩离析,有人提出分家,祖母不想,但二伯母要求强烈。老屋分成四份,成家了的大伯、二伯、三伯各一份,父亲和祖母一起一份。
我没见过祖父,常听邻居大伯说起祖父,为人豪爽,好善施,好赌。好赌的例证就是一个晚上输了七十担谷。
1949年的某个早上,一夜未归的祖父带回来十多个人,打开粮仓就往外挑谷,他对祖母说,昨晚输了七十担谷。
看着空空的粮仓,善良的祖母不吵不闹,偷偷抹着眼泪。
有人说,这个晚上祖父带着自己的大儿子、也就是我的大伯父在外面赌博,父子俩一晚上输了七十担谷,也有人说,是我祖父故意输的。
自此,祖母对儿孙的家训就是不准赌博。
老子曰:“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父亲说,如果没有输这七十担谷,也许被划为地主了。
五十年代初,纷纷烈烈的土改运动开始了。
农会主席认为:我祖父家这么多房子,还请过长工,应划为地主。
祖父去邻乡乡政府找到何某,让何某帮忙说上一句话,应该划为贫农。
何某对农会主席说:贤六阿公家为革命作过贡献,可以划为贫农。祖父的名字里有个贤字,排行第六,被晚辈叫贤六阿公。
1949年2月10日凌晨,大雪纷飞,姜亚勋、陈仲怡带领起义人员攻占了黄材警察所,大沩乡公所。同时,李石锹带领起义人员攻击了唐市警察所,这就是宁乡革命史上有名的黄唐起义。
一个星期后,起义队伍遇国民党保安队围剿被打散。3月5日,姜亚勋重新集合了一支200多人的队伍,成立湘中游击队第一支队。
5月的一天,游击队正在黄材聚会,被叛徒告密,遭保安团围剿,队伍兵分两路撤退。
一支队伍过松华河,准备从唐家湾到老鸦冲、到大冲里,到城墙大山集合。边打边撤,刚撤到厉家祠堂附近,游击队员何某大腿中弹。
外面枪声正浓,我二伯和家人躲家里往外张望,见被搀扶着一拐一拐的伤员正是他小时的朋友何某,于是,一把把他拉进房子,祖父见此,连忙把他藏到地窖里。
保安团追至此,问见到被追的人没有,祖父说,见到几个人,还有一个受伤的往厉家祠堂的后面去了。保安团一直往老鸦冲方向追去了。
何某在老屋一直把伤养好才归队。
这次撤退,是一次非常惨烈的战斗。另一支队伍,沿松华河,往沩滨中学后面梓树山撤,准备往崔坪冲,再到城墙大山会合。刚到梓树山,遭保安团大部队追击。机枪班长沈子桂留下阻击,不幸被敌人子弹打中胸口,当场晕倒在荆棘里。敌人搜山时发现了他,把他活活刺死,并割下一只耳朵回去领赏。
何某对农会主席讲了这段经历。
小时候,我也听父亲讲过这段往事。
何某还说,六阿公请的长工是姜家自己的女婿。何况,自己家里又没有田地,只是厉家祠堂的佃农。打开粮仓,空空如也,只有家里十来口人的口粮。
但还是有人不同意,有人说,毛主席那么大领导,家里有房,也是富农。
有人提出,划为中农。当时阶级成分划分,有贫农、下中农、富裕中农、地主。最后折中,定为富裕中农。
这样,老屋得以完整保留下来,如果是地主,就需分给他人。
老屋房子木材极好。听父亲讲,房子原来是铺满了楼板的。1959年至1961年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期间,房子重新分配住。祖母带着全家住到了离老屋一公里多远的松华河边,而老屋分配给了别的社员住,1961年解散食堂再回到老屋时,楼板被住户当柴火烧光了。
05
家庭成分,对于我,以及弟弟妹妹、堂弟堂妹们,影响不大,但对于我那些四十、五十年代出生的堂哥、堂姐,影响深远,甚至几代人。
堂姐敏英,大伯父的女儿,几年前,七十岁生日,她远在湖北的两儿一女,一个都没来。
我多次问过她,当年,为什么要远嫁湖北,嫁了就嫁了,有两儿一女,又为什么一定要抛夫弃子,再跑回湖南再嫁呢?每次,堂姐都欲言又止,似乎不愿提及这段往事。
他回湖南结婚后,生有一子,现在孙子也有几岁了。2019年,堂姐的湖南丈夫突发急病去世,过了几天,我去看她,又问及此事,她才缓缓说起往事。
1953年,大伯父早逝,大伯母含辛茹苦抚养着年幼的两儿一女。由于家庭成分不好,各个方面受到歧视, 特别是1966年后,大伯母常受到批斗。
逃离现实,嫁得远一点,再远一点,这就是她当时的想法。
1969年8月,宁乡暴雨成灾,一场洪水席卷全县,一千多人死伤,缺衣少吃的灾民有的远走他乡。这时,黄材村元家山有一媒婆介绍了几个年轻姑娘,嫁到湖北天门县、汉川县,嫁过去的人又回来再介绍新的人过去。
回来的人带着诱人的米糕、油炸的干鱼,把湖北描绘成了天堂。“那边是一望无际的田野,鱼米之乡,吃不完的白花花大米,嫁过去以后还有工资发。”受这样的诱惑,堂姐没告诉自己母亲,就跟着媒婆偷偷地离开了家,经过一路颠簸,又坐车又坐船,把自己嫁到了湖北汉川县。
湖北的姐夫我见过,仪表堂堂,比堂姐高很多,有1米8的个子,脸黑黑的,年龄也大很多。每年春节,堂姐、姐夫从湖北回来,带着米糕、爆米花、干鱼,从一个孩子,到两个、三个孩子。童年的我,挺高兴地跟在堂姐、姐夫后面跑,带着侄儿侄女玩。在我的眼中,觉得堂姐还是幸福的。
七十年代末,媒婆把一个有夫之妇、还有精神病的女子介绍到湖北,两边的丈夫都告状,媒婆作为人贩子被抓坐牢。有几个远嫁湖北的女子陆陆续续跑回了宁乡。
堂姐说,那时嫁过去的女子有一种被骗的感觉,虽然天门、汉川县是平原,耕地很多,但哪有什么工资发啊,也是农村里,没结婚的大龄青年有的是家庭困难,有的是家庭成分不好,她嫁的丈夫家是地主成分,原本想嫁远点,找个家庭成分好的,哪晓得是从米箩里跳到糠箩里。自己坐车又晕车,每回湖南一次不容易,看到自己母亲年纪越来越大,身体越来越不好,每次回来都舍不得她走,那边是孩子,这边是母亲,真是两难啊!看到别的女子一个个跑回来再嫁了,她也就忍心丢了那边的孩子,偷偷跑回了湖南。湖北的丈夫带着孩子来湖南找过她几次,她都躲着不见。
我问起湖北的孩子情况,堂姐眼眶里泪水在转:“这一生感到最对不起的,就是那边的儿女了!偶尔有电话联系,都结婚了,女儿女婿在深圳打工,小儿子全家住县城,过得还好,大儿子全家住乡下,困难一点。”
在儿女们心里,对忍心抛弃他们的母亲,总是有心里隔阂。
也许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活法,我不好评价堂姐他们这代人的对和错。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他们这么做,也是在特殊年代追求自己的幸福吧。
06
老屋村口的两棵古樟树,树干要几个人才能合抱得下,枝叶交叉,重重叠叠,树冠像一把巨伞,遮阴避雨。有人说这是夫妻树,至少有两百年以上。外出的村民回村远远看到老樟树,就到家了,就心安了。
夏日,全村的人喜欢坐在樟树下乘凉、聊天,地上常常铺满了一层黑黑的樟树籽,凉风习习,树叶婆娑,树顶上常有用干樟树枝搭建的喜鹊窝。如果一夜大风,早上可以在樟树下捡上一大篓干树枝。
大人说,这是一棵神树,树皮可以做药,可以醒酒,所以,常常见树干的树皮被人割走。
夜晚,搬上竹床、竹椅,坐在树下听那几个读过一点书的大人讲“白话”(故事)。有白蛇娘娘的故事、孙悟空大闹天宫、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聊斋的故事。夜越深,就越是讲鬼故事,白骨精就躲在樟树上,聂小倩、婴宁今晚会来找你。吓得孩子们一哄而散,各自跑回家。
一个没有月光的晚上,我一个人从外面回家,远远就听到樟树上有“呜哇——呜哇——”的叫声,我快速往家跑,只见一个黑影嘘的一声,从我身边往樟树上飞去。吓得我回家扑在母亲怀里哇哇大哭:“我看见鬼了,我看见鬼了!”
第二天,母亲把外婆接来给我“收吓”。那时候,外婆常常给受惊吓的孩子“收吓”,先泡上一把浓茶,外婆把孩子的小手一个指头一个指头的握一下,然后握成拳头,握紧在她的大手里,再用茶水在孩子额头上弹三下,再喝上一口茶水就好了。奇怪的是,“收吓”后,受惊吓的孩子果然就好了。
八十年代初,我到外地上学,第一年寒假回家,下了车,往老村走去。
那棵老樟树呢?村口坡上那两棵老树呢?是不是我走错地方了?我的心空空的。
老樟树没了,很多很多树也没了。
父亲给我讲了砍树的经过。
生产责任制,分田到户。把田分了,把生产队的农具分了,把耕牛分了,紧接着,把山也分了,把村前的树也分了。
这棵几百年的老樟树也分了,4户人家共同拥有。是不是把这棵树砍了分了,虽然发生了分歧,但最终老树没有逃过厄运。
砍树那天,全村的人都在围观,老樟树轰然倒下的那一刻,老人们眼里噙满泪水。
老樟树没了,老村的灵魂丢了,外地游子回村远远地看不到老樟树,心也慌了。
如同这棵老樟树的命运一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集体的山林分到农户前,普遍遭受一次厄运,山上树被砍光。
一年后,牵头砍老樟树的村民在一次维修电路时,意外触电身亡。有人说,是神树老樟树在显灵。
07
住在老屋,父亲总得病,我和弟弟也病,有一次,我和弟弟同时病了,父亲用箩筐挑着我俩,去镇上卫生院看病。
老屋旧了,破了,只想搬离老屋。
1978年,集体经济有所好转,原来一天的工分只有几角钱,这时可以接近2元一天了。我家拆了老屋的两间房子,用这些木材到新的地方建了四间平房。
老屋的砖缝里发现有发黄的字纸,光绪年间的。
那些老土砖敲碎以后,运到田里作肥料。
以后,伯父、堂哥以及邻居陆陆续续、一个个拆了老屋,大部分人家搬离了老村,在离公路近的地方建了新房,少数在原地重建了独立的楼房和平房。
老村的四合院消失了。
08
当我到岳阳县张谷英村,到安徽黟县宏村,看到那种老村、老屋,那种露天四合院,总会想起儿时也曾生活在这样的老村,这样的老屋。
如今,这样的老屋在宁乡已经很少。
想起宋朝裘万顷所咏《老屋》:
老屋久欹侧,随宜聊拄撑。
吾今且共住,缘尽会须行。
雨打从教坏,风摇不用惊。
世间虚幻相,聚散本无情。
“缘尽会须行”“聚散本无情”。人世间的一切是不是都是“虚幻相”?人世间聚散是缘分,与老屋的缘分也一样。
八十年代末,第一次到女朋友家,她说起贺石桥乡政府的青砖瓦房。于是,我们兴高采烈地骑着自行车,从洪仑山出发前往贺石桥乡政府。
青砖瓦房,走过悠长的回廊,青石板地,大天井,大花坛,正有栀子花盛开。贺石桥贺家祠堂,是北伐名将、国民党高级将领贺耀组的故居。
从贺耀组老屋出来,路边一小女孩背着背篓,身边一只小花狗,自行车经过时,小花狗突然从车前跑过,我一急刹,车和人倒在地上,小女孩急忙过来说对不起,我和女友拍拍身上的灰说,没事,没事。
二十八年后,在长沙偶遇一贺姓女子,她说老家是贺石桥乡政府边上的。我问起贺耀组故居是否还在,她说早在九十年代就全部拆了,一点痕迹都没了。我说起当年路边遇到的小女孩,她说小女孩就是她,她当年十二岁,对那件事记忆犹新。
我唏嘘不已,这个世界太小。
09
电视里,听白岩松朗诵《长大回家》:
“长大回家,又有几天可以不用说普通话,老友相聚,合影像一张泛黄的油画,我们认真地排着谁小谁大,如果童年游戏再玩一下,还是想和你对家”“长大回家,让我们一起唱往日时光吧,歌声中我回到桌边把剩酒悄悄喝下,突然眼中全都是泪花,别怕,这正是最好的年华。长大回家,唱往日时光的我们就在最好的年华。”
其实,当你总是喜欢回忆的时候,感觉自己老了。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如今,对余光中的《乡愁》有了更深刻的感受。
父母不在了,但春节、清明、农历七月半总要回老家。
我常会回到老屋的地方看看,在长满杂草的老屋地基寻找那只蟋蟀、寻找墙隙里的那只七星瓢虫、那只蜜蜂,寻找我的童年。
原来的住户大多搬走了,一片绿绿的菜地,一片斑驳的灌木杂草。我想,如果在这里再建房子多好。可是,户口不在这里,回不去了。
人生就是这样,只能往前走,不能走回头路。
比我小半岁的堂弟,我二伯父的儿子,幼时,父亲早逝,母亲改嫁,年轻时,他把老屋拆了,卖了,远走南方打工,漂泊了半辈子,仍是孤身一人。
几年前,他回到老屋地基,原地建了三间房子。搬进新房的当晚,他父亲来到床前,说很久没吃肉了,他回答,家里没有猪肉,只有牛肉,他父亲回答说,牛肉也想吃。原来是南柯一梦,惊出他一身冷汗。
第二天一早,打开冰箱一看,果然只有牛肉,按照老家风俗,牛肉是不用来敬神的。他忙去买了猪肉、鸡、鱼,祭祀一天。如此,再没做类似的梦。
老屋其实一直在的,在每个人的灵魂里。
作者简介
姜峰,本名:姜太军,湖南宁乡人,当过高校教师,副教授,湖南省散文学会会员,现供职于湖南某省直单位,出版有散文集《文旅观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