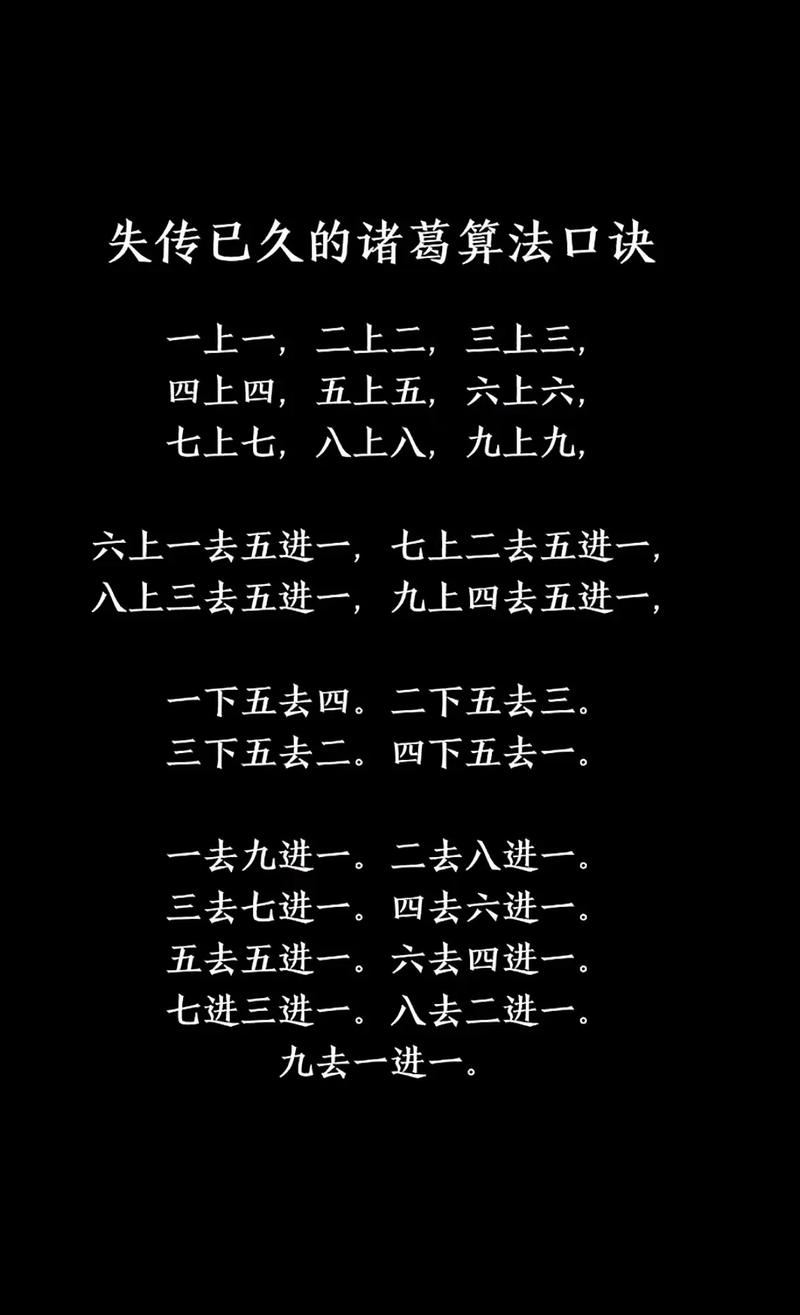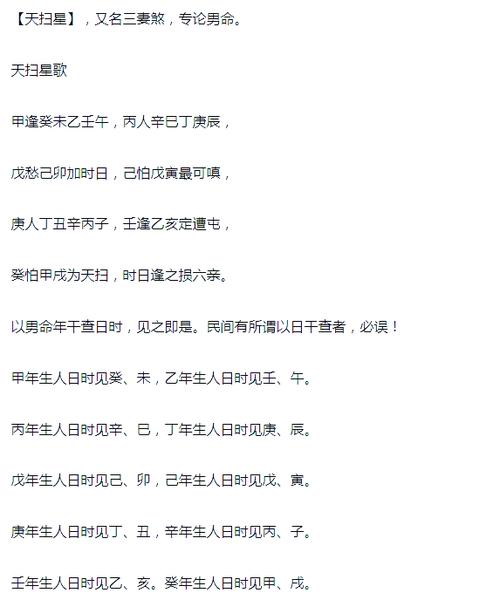石炭井,回不去的家园
进了石炭井,迎面就是不长的一个下坡。坡到了不远处的一座小桥,才变得平坦了。路的东西两边,是父亲上班的一矿的五座五层商品楼。坡的中段,路的西边,是我原来的家——商品五楼。
马路对面,则是东一家西一家的平房,每家有一个很大的院子,种着一棵棵绿绿的枣树。
那次陪妹妹去石炭井办事,刚一进沟口,就急切的想看看自己原来的家。到了石炭井,坡的两边一直到小桥那段路,没有了任何遮挡,一大片平地,种了一棵棵树冠不大的小树。远处矿区边上的矸石山,高大、突兀。坡的中间,路的西边,没有一点我原来家的影子。
我一时有点发蒙,像一个人站在空旷的荒原。
路边那几棵歪歪扭扭的老槐树还孤零零的立着,那棵往路上歪者身子,最大的一棵槐树,还是那么歪着。我依稀记得它那根最粗的枝杈,正对着我家的单元。可现在那根粗大的枝杈,指着空中呼呼刮过的山风。
根据一棵多年不见的树,根据一棵树的一根枝杈,我才找到我家-一套将近七十多平米二层楼房的旧址
我家原本住的是平房,烧炉子,冬天靠火墙取暖。父亲嫌烧煤麻烦——夜里要起来一两次,给炉子加煤。长期下井的父亲,冬天怕冷,平房冬天到底不够暖和。
一九八八年,父亲就花几千块钱买了这套楼房。房子白灰墙、水泥地,不用任何装饰,就可以直接搬进去住。房子前后有两个阳台。
前面的大阳台正对着马路。站在阳台上,可以看到马路上的人来车往。路对面,不远处,是光秃秃灰白的贺兰山。后面厨房的小阳台,正对着矿上轰隆隆的铁路和高大的矸石山。
那段时间石炭井往出搬的人家慢慢的多了。隔段时间,就有一辆卡车,装满一车的家当,在我家楼下,嗡嗡嗡极不情愿得慢慢地爬坡。
一辆车就装了一个家,石炭井还在,可家又少了一个。
家里就父亲一个单职工,母亲一直闲不住,忙这忙那,挣点零花钱贴补家用。去矸石山捡破烂;到矿上卖瓜子;守着桥头卖菜;在家里织手套。
有一年年母亲想养兔子和鸭子,就四百块钱买了马路对面我同学家的平房,带一个大大的院子。母亲主要是看上了那个大院子。
母亲和父亲就在附近四处捡砖头,加高加固院子的围墙,砌了几个兔子窝和鸭子窝。
院子前面有一处房子,据说是一个杀猪匠扔下的。有些孩子想拿废铁卖钱,就把那处房子拆的七零八散,只余断壁残墙。母亲把这家的后院墙扒掉,和我家的院子连了起来。
在这家的屋檐下,母亲捡到了四百块钱,那可能是杀猪匠顺手塞下的私房钱吧。母亲用四百块钱买了这处院子,杀猪匠替我们付了钱。杀猪匠又怎么知道,他还买过那么大的一个院子呢。
大学毕业,我去了红果子上班。结了婚,又去了另一家大武口的单位,并把家安在了大武口,算是在大武口站住了脚。在大武口住了这么多年,我熟悉每个街道、小路,熟悉每一个小区。
望着巍巍的贺兰山,我总是觉着,山那边,才是我这辈子真正的家。
后来,和我一起在红果子同一个单位上班的大妹妹、大妹夫,也辗转把家安在了大武口。大妹妹磨豆腐、卖粮油、送报纸、卖衣服,也算是在大武口扎了根。在石炭井医院的小妹妹,结婚后,费了几年的功夫,调到了大武口,也把家搬到了大武口。
就剩下父亲和母亲,孤零零的住在石炭井。
总是觉得有股挺大的风,在后面推着你,一天天往某一个地方走。在风中,我慢慢的有了白发。看近处的东西,摘了眼镜,反而看的更为清楚。
风一天天的吹刮,我不知道这辈子还会被风刮到哪去。
石炭井的人家越来越少,我们都劝父亲、母亲搬下来和我们一起住。夏天大武口热,蚊子多。冬天呢,大武口又太冷。石炭井是个山沟沟,夏天凉快,冬天也没那么冷。执拗的父亲一再找各种借口,就是不愿意搬下来。
石炭井的大部分退休人员都从山上搬了下来。政府给退休工人盖的安置房,只在大武口盖最后一批了,以后就盖到南沙窝去了。南沙窝到底是远些,住的离我们做子女的远了,总归不方便。
石炭井实在是住不成了,父亲才很不情愿的往下搬。
父母的家总共搬了两次。
第一次我租了个大卡车,两个妹夫回去帮着搬的。这次是把那些大件的家具往下搬。母亲这也舍不得,那也舍不得。按她的话说,连根小棍都要带走。大妹夫无奈给我打电话,说搬家的车已经装的满满当当,可是母亲还要往车上塞东西,怎么说就是不听。我听了也是哭笑不得,我去劝,又有什么用呢。
第二次我托朋友找了辆车,自己找了两个要好的同事帮着搬。这一回就剩了锅碗瓢盆、瓶瓶罐罐。又是装了满满的一车。母亲屋里转了几圈,院子里又转了几遍,生怕拉下什么。
车在路边等了好是一阵,母亲才最后从老房子里出来,提了一个旧提篮,里面是三个石嘴山白瓷厂的蓝边白瓷碗,一个七十年代的大搪瓷盘。
我一定用过中间一个碗喝过稀饭,吃过面条。过年的时候,那个搪瓷盘里摆满了瓜子、糖块、花生,放在两只沙发中间的小桌上。冬天的阳光,透过窗户,暖暖的照着。那阳光里,淡淡的炉烟,轻轻的漂浮。
上车前,父亲悄悄的跟我说,能不能让车从街里头转上一圈,好在最后看一眼石炭井。看看西天的太阳,想着母亲耽误了不少时间,刚才听说司机师傅着急回去有事,也就没好意给司机师傅说。父亲也就没有吭声。
车,终于开了。
父亲一直望着窗外,像个好奇的孩子,第一次来到这里。母亲一只胳膊挎着那只提篮,默默的不说话。拐过一个个弯,我往后望去,蜿蜒起伏的山路,在后面越来越远,像一首委婉悠长的老歌。
我的心头一阵阵发堵。
车开的慢慢的,不知道司机师傅是怕颠坏车上的瓶瓶罐罐,还是想慢一点,让父亲多看一看那窗外的过去。
出了沟口,车明显的快了起来。车上还是没有人说话,只是那沙沙的车轮声,响个不停。
我们来石炭井的第一个家,在双桥街一矿大食堂马路对面的自建房。自建房都是依势而建,门到底是朝哪开,全都要看下面的地势来定。
那片自建房,就像胡乱扔在地上的一堆木箱子。
一九八五年农转非,全家都成了城里人,从老家农村搬到了石炭井。父亲就不能再一个人住单身宿舍,必须得有一套房子了。一九八四年年,父亲就花了八百块钱,买了这套平房。房子带一个不小的院子,在一个不长的巷子里面。
一九八五年的暑假,我和大妹妹,先跟父亲来了石炭井,留下母亲和小妹妹,收拾老家最后的家当。
那天临近中午,我们在一矿食堂对面下了车。我们三个直接来到了新房子里。窗户上挂着蓝色竹子图案的清爽的窗帘,地上的水泥地平平的,顶棚整整齐齐的糊了新的报纸,白墙也明显的重新刷过,火墙也都换了新的红砖。看着齐整整的一切。
看着齐整整的家当,我由衷的赞叹这房子真好,父亲在旁边自豪的说,不知道废了我多少工夫。
入秋不久,母亲和小妹妹也来了,在石炭井,我们有了一个完整的家。
总是闲不住的母亲,又有了一显身手的一方小天地。母亲在院子西南角砌了个小棚,摆放上钢筋焊成的一个大鸡笼,养了一笼的鸡。每天上学前,我会把烂菜叶剁碎,和上鸡饲料去喂鸡。
夏天种了一园子的西红柿,家里定点供水,水不够用。一个暑假,每天我要去公共水龙头,挑回来一桶桶的水,去浇西红柿。园子靠近过道的边上,种了一溜鲜艳的大丽花、地雷花。低矮的围墙上面,又摆了几盆花。
一九八八年,家里买了套楼房,就卖了这套平房。房子,在我们手里老了四年。四年,说起来也不算短。
我们在院子里砌了个炉子,盖了小棚,焊了鸡笼,加高了院墙,地里施加了肥料。这房子在我们手里实际上又新了四年。卖的时候,又卖了个原价。
那两年,石炭井陆陆续续的拆迁,一个周末,我和初中同学房向华坐车去石炭井拍照片。到了一矿大食堂,我急切的走进那个小巷子去看我曾经的家。
破旧的院门松松垮垮的关着,门上的“福”字耷拉下一个角,两边的对联发白破烂,残缺不全。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住,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又换了人家。
我不忍心去敲门,我怕门一开,满院子过去的事,又呼啦一下子跑出来。我怕看到过去自己的影子。我也怕看到过去家里人的影子......
回头看了几眼,我赶紧坐上车,再去别的地方。
好几次,说起石炭井,我会问母亲,回石炭井吗?我带你回去。母亲总会叹口气,说不回。我问为啥,母亲说回去心里难受。母亲随即就岔开话,说起别的事情。
平时说道石炭井,遇到不确切的事情,我总会给父亲、母亲打电话,让我惊讶的是,再模糊的事情,父亲、母亲都记得真真切切,精确到一个个极小的细节。
是的,记到心里的事,怎么能随随便便的忘记呢。
我知道,石炭井一直在父亲、母亲的心里。
不只一次,在梦里,我们将自己还在石炭井。总是梦见自己放学后,背着书包,回了平房。推门进去,说,妈,我回来了。没有人答应,炉子上烧着水,嘶嘶的冒着热气。案板上放着切好的葱、姜、蒜,一小堆的土豆丝,几片西红柿。进了里屋,四处看看,没有一个人。
还会梦见自己放学后,回了家里那套楼房。门口的饭桌上摆着几牙西瓜,旁边一个铝盆里,几块啃过的瓜皮。旁边一个搪瓷缸子里,半杯褐色的浓浓茶水。几个屋子看看,没有一个人。
去到大阳台,看见楼下的坡上,搬家的车,装满了一车子的家当,艰难的慢慢嗡嗡嗡的爬坡。两位放学还没到家的同学,有说有笑的越走越远。来到厨房里的小阳台,后面烟雨中的贺兰山,高低朦胧。
每次醒来,都会再也睡不着。心里有一层黑夜一样厚重的惆怅,压得我胸闷。
石炭井还在,家没了,回家的路没了。寂静的白天,寂静的黑夜,只有那呼呼的山风,还一天天地吹刮个不停。
石炭井,我再也回不去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