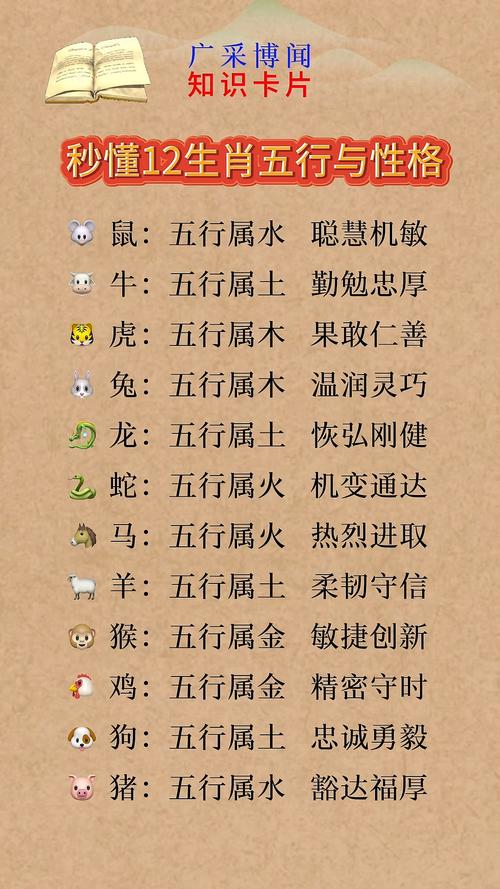秘密:我去世的奶奶托梦给我,说她埋了一箱金子,我挖开后傻眼了
奶奶是头七那天晚上来的。
我正睡得昏昏沉沉,感觉有人在轻轻拍我的脸。
那力道很轻,带着一股熟悉的、皂角和阳光混合的味道。
我眼皮沉得像灌了铅,怎么也睁不开。
“然然,我的然然。”
是奶奶的声音。
干瘪,沙哑,像秋天被风吹得哗哗响的苞米叶子。
我心里一酸,眼泪就隔着眼皮往外冒。
“奶奶。”
我在梦里喊她,声音小得像蚊子哼哼。
“奶奶给你留了东西。”
她还在拍我的脸,一下,又一下。
“就在院里那棵桂花树下头,我埋了个箱子。”
“啥箱子?”我迷迷糊糊地问。
“一箱金子。”
她说得笃定,不容置疑。
“给你当嫁妆的,那时候没来得及。你自己去挖,别便宜了别人。”
金子?
我脑子“嗡”的一声,像是被谁敲了一记闷棍。
那点睡意瞬间跑得无影无踪。
我猛地睁开眼。
天花板。白色的。
陈阳睡在旁边,呼吸均匀,还带着轻微的鼾声。
屋里一片寂静,只有空调出风口细微的“嗡嗡”声。
哪里有奶奶。
哪里有皂角和阳光的味道。
就是一个梦。
我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眼泪终于忍不住,湿了一大片。
奶奶走了,就在一周前。
走得很急,脑溢血,从发病到咽气,不到二十四个小时。
我连她最后一面都没见上。
第二天早上,我顶着两个硕大的黑眼圈起床。
陈阳正在厨房煎鸡蛋,油“滋啦滋啦”地响。
“你昨晚做贼去了?”他端着盘子出来,看我一眼,皱起了眉。
我没说话,拿起一片吐司,机械地往嘴里塞。
“我梦见我奶奶了。”我嚼着面包,含糊不清地说。
“嗯,正常。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嘛。”陈阳把煎蛋推到我面前,“多吃点,今天还得上班呢。”
我看着盘子里那个边缘焦黄、溏心晃荡的鸡蛋,一点胃口都没有。
“她说,她给我埋了一箱金子。”
陈阳正喝着牛奶,听到这话,“噗”的一声差点喷出来。
他呛得满脸通红,咳了半天。
“你说什么?”他瞪大眼睛,像看一个外星人。
“我奶奶,托梦给我,说在老家院子的桂花树下,埋了一箱金子。”我一字一句,重复了一遍。
陈阳放下牛奶杯,一脸“你是不是发烧了”的表情,伸手探了探我的额头。
“不烧啊。”他自言自语。
然后他坐直了身子,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林然,我知道你难过。奶奶刚走,你心里不好受,胡思乱想也正常。”
“可这个梦太真实了。”我急了。
“梦都是真实的,不然怎么叫身临其境呢?”陈阳开始给我上哲学课,“你就是太累了,压力太大。要不今天请个假,在家好好歇歇?”
“我没疯!”我提高了音量。
我的声音在不大的餐厅里回荡,显得格外突兀。
陈阳愣住了。
我们俩就这么对视着,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焦糊的蛋味和尴尬。
最后,他妥协了。
“行,行,行。你说有就有。”他举起双手,做出投降的姿势,“那……你打算怎么办?买张票,扛着锄头回老家挖宝去?”
他的语气里带着七分调侃三分无奈。
我被他噎得说不出话。
是啊,怎么办?
跟老板请假,说我奶奶托梦给我一箱金子,我要回家去挖?
老板不把我当精神病送进医院才怪。
这件事就在我和陈阳之间,成了一个心照不宣的、略带诡异的秘密。
我没再提,他也装作忘了。
可我忘不了。
那个梦像一颗种子,在我心里扎了根,疯狂地发芽。
上班的时候,我对着电脑屏幕发呆,眼前晃动的全是奶奶那张布满褶子的脸。
开会的时候,老板在上面慷慨陈词,我耳朵里听见的却是奶奶那句“一箱金子”。
我开始失眠。
一闭上眼,就是老家那个小院。
院子不大,水泥地,角落里种着一棵桂花树。
那是我爷爷在我出生的那年种下的。
我小时候,每年秋天,奶奶都会把打下来的桂花晒干,做成桂花糖、桂花糕,还有香喷喷的桂花茶。
那棵树下,是我童年全部的乐园。
我会不会,真的像个傻子一样,信了一个梦?
可那不是普通的梦。
那是奶奶。
是那个把我从小带大,有好吃的第一个塞给我,受了欺负第一个护着我的奶奶。
她从来没骗过我。
一个星期后,我彻底扛不住了。
我瘦了五斤,眼窝深陷,整个人像被抽走了精气神。
陈阳看我的眼神,从最初的调侃,变成了担忧。
“然然,我们去看医生好不好?”他小心翼翼地问。
我摇摇头。
“陈阳,”我抓住他的手,指甲几乎要嵌进他的肉里,“你陪我回一趟老家吧。”
“就当是……回去看看。”
“就当是,陪我疯一次。”
他看着我,看了很久很久。
久到我以为他又要开始长篇大论地教育我。
但他最后只是叹了口气。
“好。”
他说。
“我陪你回去。”
“不过说好了,就这个周末。挖不出来,你得答应我,把这事彻底忘了,好好过日子。”
我用力点头,眼泪差点掉下来。
周六一大早,天还没亮,我们就出发了。
老家在邻市的郊区,开车要三个多小时。
奶奶走了以后,老房子就空了下来。我爸妈早就住在城里,一年也难得回去一次。
车开出市区,高楼大厦渐渐被低矮的平房和绿色的田野取代。
我摇下车窗,一股混合着泥土和青草味道的潮湿空气涌了进来。
我的心跳得有点快。
既期待,又害怕。
期待那个梦是真的,害怕它只是一个梦。
如果挖出来什么都没有,我该怎么面对陈阳那张“我早就说过”的脸?
又该怎么面对自己这份近乎偏执的愚蠢?
车在一条窄窄的村道上停下。
前面就是奶奶家那熟悉的灰色二层小楼。
只是现在,它看起来那么安静,甚至有些萧瑟。
门上还贴着白色的挽联,被风雨打得有些褪色破损。
陈阳从后备箱拿出我们准备好的工具。
一把崭新的工兵铲,还是他特意网购的,说是“多功能,折叠便携”。
我看着那把亮闪闪的铲子,突然觉得有点滑稽。
我们俩,两个标准的城市白领,现在要拿着这玩意儿,在一个乡下院子里,根据一个虚无缥缈的梦,去挖所谓的“金子”。
这事儿说出去,谁信?
我拿出钥匙,打开了那扇熟悉的木门。
“吱呀”一声,像是老人的一声叹息。
院子里的景象,和我记忆中差不多。
只是水泥地上积了一层薄薄的灰尘,角落里长出了几丛杂草。
那棵桂花树,依旧立在院子的西南角,枝叶繁茂,只是还没到开花的季节。
我径直走到树下。
就是这里。
梦里,奶奶就是指着这片地方。
我蹲下身,用手扒拉了一下地面。
是坚实的泥土,上面还覆盖着一些陈年的落叶。
“就这儿?”陈阳走过来,用脚踢了踢地面。
“嗯。”
“看起来……不像埋过东西的样子啊。”他嘟囔着。
“埋了几十年了,当然看不出来。”我不服气地反驳。
“行吧。”陈阳把工兵铲递给我,“你打算从哪儿下手?”
我环顾了一下树根周围。
“就……就从这儿吧。”我随便指了个地方。
说实话,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奶奶只说了在树下,可没说具体哪个位置。这树根盘根错节的,范围可不小。
陈阳没说什么,把袖子一卷,接过铲子。
“我来吧,你歇着。”
他看起来还是不怎么相信,但行动上却很配合。
这大概就是他表达爱的方式。
一边吐槽你,一边舍不得你受累。
第一铲下去,挖开了表面的浮土。
第二铲,第三铲……
陈阳到底是男人,力气大。没一会儿,就在地上挖出了一个小坑。
泥土被翻起来,散发出一种特有的腥气。
我蹲在一旁,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个越来越深的坑,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叮!”
一声清脆的声响。
铲子好像碰到了什么硬物。
我和陈阳同时对视了一眼。
彼此的眼睛里,都闪着一丝不敢相信的光。
“有东西?”我声音都发颤了。
“好像是。”陈阳也严肃起来,他扔掉铲子,趴在地上,用手去刨。
我也赶紧过去帮忙。
我们俩像两只刨土的狗,灰头土脸,狼狈不堪。
很快,一个硬硬的、方方正正的轮廓出现在眼前。
不是箱子。
是一块红砖。
……
空气瞬间凝固了。
我看着那块砖,又看看陈阳。
他脸上的表情很复杂,像是想笑,又得憋着。
“咳。”他清了清嗓子,“失误,失误。这盖房子的时候,剩下几块砖埋土里也正常。”
我没说话,默默地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
一股巨大的失望和羞耻感涌了上来。
我就像个彻头彻尾的傻子。
“要不……算了吧?”陈阳试探着问,“天挺热的,别中暑了。”
“不行!”
我几乎是吼出来的。
“接着挖!”
我抢过他手里的铲子,换了个地方,开始疯狂地挖起来。
我也不知道自己哪儿来的力气。
我只想证明,我不是个傻子,奶奶没有骗我。
陈阳看着我,没再劝。
他只是默默地拿了瓶水,拧开盖子,递到我嘴边。
“慢点,不急。”
那天下午,我们把桂花树下,能挖的地方,几乎都翻了一遍。
一个坑,两个坑,三个坑……
院子里一片狼藉,像是被野猪拱过一样。
除了挖出几块砖头,一个碎掉的玻璃瓶,还有一条早就生锈的铁丝,我们一无所获。
太阳渐渐西斜,把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
我终于没了力气,一屁股坐在地上,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和泥土混在一起,一道一道的。
手心火辣辣地疼,磨出了好几个水泡。
完了。
什么都没有。
就是一个梦。
一个荒唐的,可笑的梦。
我把脸埋在膝盖里,肩膀控制不住地颤抖起来。
我不是为金子哭。
我是为我的那份执念,那份可笑的坚持。
更是为了那份再次被确认的、失去奶奶的巨大的空洞感。
陈阳走过来,在我身边坐下,轻轻揽住我的肩膀。
“好了,好了,不挖了。”他的声音很温柔,“我们回家。”
“是我太傻了,对不对?”我闷声说。
“不傻。”他拍着我的背,“一点都不傻。你想奶奶了,我也想。回来看看,挺好的。”
就在这时,邻居王阿姨家的门开了。
她端着个碗,探头探脑地朝我们院子里看。
“哎哟,然然,陈阳,你们回来啦?”
王阿姨是个热心肠,也是个大嗓门。
她看到院子里这副景象,吓了一跳。
“你们这是干啥呢?院子里招白蚁了?”
我窘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陈阳倒是反应快,立马站起来,笑着说:“王阿姨,没事儿,我们看这树长得不好,想给它松松土。”
“松土?”王阿姨一脸不信地走过来,“松土用得着挖这么大坑?跟要掘地三尺似的。”
她走到我们挖的最后一个坑边上,伸头看了看。
“哎,你们挖这儿干嘛?”她突然一拍大腿,“这地方不能挖啊!”
我跟陈阳都愣了。
“怎么了?”
“这树底下,以前是连着你家老灶的烟囱根儿啊!”王阿姨指着那个坑,“后来你爸妈嫌烧柴火麻烦,改成煤气灶,就把灶台拆了,这烟囱根就埋在下面了。你们再挖,当心把地基给挖松了!”
烟囱根?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一个被我遗忘的画面,猛地闪了回来。
小时候,奶奶家的厨房还是那种老式的土灶。
灶台很大,连着一个粗粗的烟囱,烟囱的出口就在屋外的墙上,离桂花树不远。
奶奶总是一边烧火,一边给我讲故事。
她说,灶王爷就住在这里面,我们说什么话,他都听得见。
后来爸妈装修房子,把土灶拆了,换成了亮晶晶的瓷砖和煤气灶。
我好像是哭了一场,觉得我的灶王爷没地方住了。
“烟囱根……”我喃喃自语。
奶奶的梦,会不会另有玄机?
她说的“桂花树下”,会不会不是指树根底下,而是指……和树有关的,别的地方?
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移向了那面连着厨房的外墙。
墙上,因为常年被烟火熏燎,有一块明显的、比周围颜色更深的印记。
那正是当年烟囱口的位置。
它就在桂花树的枝叶掩映之下。
一个疯狂的念头,再次冒了出来。
“陈阳。”我抓住他的胳膊,声音都在抖,“墙。”
“墙?”他没明白。
“挖墙!”
陈阳的表情,比刚才看到红砖时还要精彩。
“林然,你冷静点。我们是来松土的,不是来拆房的。”
“你信我一次,就最后一次!”我几乎是在恳求他,“王阿姨不是说了吗,这里以前是烟囱。烟囱是空的!”
“奶奶会不会是把东西藏在烟囱里了?”
陈阳看着我,又看看那面墙,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
“就算藏在里面,那也早就被封死了。我们怎么拿?”
“砸开!”
我说得斩钉截铁。
王阿姨在旁边听得目瞪口呆。
“然然,你可别乱来啊。这房子虽然老,可还是好好的。你这一锤子下去,墙要是塌了可怎么办?”
“王阿姨,没事的,我就轻轻敲一下,看看是不是空的。”
我说着,就从院子角落里捡起半块砖头。
陈阳想拦我,已经来不及了。
我走到那片烟熏火燎的墙壁前,深吸一口气,闭上眼,拿着砖头,凭着记忆中烟囱口的大概位置,用力敲了下去。
“咚!”
一声闷响。
是实心的。
我的心,沉了下去。
陈阳松了口气,走过来想拉我。
“我就说……”

他的话还没说完,我又举起了砖头,往旁边挪了大概十厘米,再次敲了下去。
“叩叩!”
这次的声音,完全不一样!
是空的!
里面是空的!
我激动得差点跳起来。
“听见没!是空的!”
陈阳也听见了,他脸上的怀疑,瞬间变成了震惊。
他抢过我手里的砖头,对着那个位置,又敲了两下。
“叩叩,叩叩。”
千真万确。
“真……真是空的?”他喃喃道。
“快!找个锤子!”我催促他。
王阿姨也反应过来了,转身就往自家跑。
“等着,阿姨家有锤子和凿子!”
很快,王阿姨拿着工具回来了。
陈阳接过锤子和凿子,对着那个发出空响的地方,摆好了架势。
“我可真砸了?”他最后确认了一遍。
我用力点头。
“砸!”
“哐!哐!哐!”
陈阳卯足了劲。
墙上的水泥块和石灰开始剥落,露出里面的红砖。
他又对准砖缝,用凿子一点点地凿。
这是一个细致活,比刚才挖土累多了。
汗水顺着他的额头往下淌,打湿了睫毛。
我站在一边,紧张得手心冒汗,连大气都不敢出。
终于,随着“咔”的一声,一块砖松动了。
陈阳小心翼翼地把砖头抽了出来。
一个黑乎乎的洞口,出现在我们面前。
他拿手机打开手电筒,往里照了照。
“有东西!”他压低了声音,语气里是掩饰不住的兴奋。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是什么?”
“看不清,被布包着。我……我够不着。”
洞口太小了,他的胳膊伸不进去。
“我来!”
我比他瘦,胳膊细。
我把袖子撸到最高,把半个身子都贴在墙上,将胳膊奋力往洞里伸。
指尖,触到了一个粗糙的、包裹着什么东西的布料。
很硬。
我用手指勾住,一点一点地往外拖。
那东西还挺沉。
终于,在我和陈阳的合力下,那个被灰尘和时光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被我们从墙洞里拖了出来。
它外面裹着好几层油布,已经变得又硬又脆。
最外面还用麻绳捆得结结实实。
我看着这个包裹,突然不敢打开了。
“打开看看啊。”陈阳催促道。
我点点头,深吸一口气,开始解那根早就已经和油布黏在一起的麻绳。
绳子很脆,一用力就断了。
我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地揭开油布。
里面,露出了一个木箱子的边角。
是一个上了年头的、颜色暗沉的木箱。
上面还挂着一把小小的、已经锈迹斑斑的铜锁。
我的心跳得像打鼓。
就是它!
奶奶梦里说的那个箱子!
“金子……”我喃喃道。
陈阳也咽了口唾沫,眼睛瞪得溜圆。
王阿姨更是伸长了脖子,恨不得把眼珠子贴到箱子上来。
“锁住了,怎么办?”
“砸开!”陈阳这次比我还果断,拿起锤子就要动手。
“别!”我拦住了他。
我不想这么粗暴地对待奶奶留下的东西。
我仔细看了看那把小铜锁。
突然,一个念头闪过。
我从脖子上取下一把一直挂着的钥匙。
这把钥匙很小,样式很旧,是我小时候在奶奶的首饰盒里翻出来的。
奶奶说,这是她年轻时候锁日记本的钥匙,后来本子丢了,钥匙就留了下来。
我觉得好看,就串了根红绳,一直挂在脖子上,当个护身符。
这么多年,都习惯了。
会不会……
我颤抖着手,把那把小小的、已经有些发黑的钥匙,插进了锁孔。
大小,正合适。
我轻轻一拧。
“咔哒。”
一声轻微的,却如同天籁般的声响。
锁,开了。
我的眼泪,刷地一下就流了下来。
原来,奶奶早就把钥匙交给了我。
我吸了吸鼻子,怀着一种近乎朝圣的心情,缓缓地打开了箱盖。
那一瞬间,我们三个人都屏住了呼吸。
没有想象中金光灿灿的景象。
箱子里,没有金条,没有金元宝,什么金子都没有。
满满一箱子,装的竟然是——钱。
一沓一沓的,全是旧版的,印着两个女拖拉机手头像的,一元纸币。
纸币很旧,边缘都起了毛。
每一沓都用橡皮筋捆着,码得整整齐齐,几乎塞满了整个箱子。
我傻眼了。
陈阳傻眼了。
王阿姨也傻眼了。
“这……这是啥啊?”王阿姨最先反应过来,“怎么全是……一块钱的?”
我伸手,拿起一沓钱。
橡皮筋早就老化了,一碰就断了。
纸币散开,一股陈旧的、混合着樟脑丸和时光的味道扑面而来。
我随手拿起一张,纸币软软的,上面似乎还留着奶奶指尖的温度。
这算什么?
奶奶说的金子,就是这一箱子一块钱?
我脑子一片混乱。
是奶奶记错了?还是她在跟我开玩笑?
可她从来不是个会开玩笑的人。
“这得有多少钱啊?”陈阳蹲下来,拿起一沓,数了数。
“这一沓是一百块。”
他又看了看箱子。
“这一层大概有二十沓,就是两千块。这箱子……我估计得有五六层。”
五六层……
那就是一万多块钱?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万多块钱,确实是一笔巨款。
被称为“万元户”,是富有的象征。
可放在今天……
我和陈阳一个月的房贷都不止这个数。
巨大的失落感,比刚才挖不出东西时还要强烈。
原来,我折腾了这么久,费了这么大劲,换来的,就是一万多块钱的旧版纸币。
甚至都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在银行兑换。
“哎。”王阿姨叹了口气,“你奶奶也是……这钱放银行存个死期,也比现在多啊。”
是啊。
我苦笑了一下。
奶奶不识字,一辈子没去过银行。
她只相信把钱放在自己看得到的地方。
“然然,你看,底下还有东西。”陈阳突然说。
我探头过去。
在箱子底部的角落里,那些纸币下面,还放着一个用手帕包着的小东西,和一封信。
信封已经黄得厉害,上面没有字。
我小心翼翼地拿出那个手帕包,打开。
里面,是一个小小的、样式简单的银手镯。
手镯已经氧化发黑,但能看出做工很细致,上面刻着细小的花纹。
这个手镯我认得。
奶奶在世时,一直戴在手上。
她说,这是爷爷当年送给她的定情信物。
后来她年纪大了,手腕变粗,戴不进去了,就收了起来。
我没想到,她把这个也放进了箱子里。
我的手颤抖着,拿起了那封信。
信纸很薄,是那种最老式的、带横格的信纸。
信上的字,不是奶奶写的。
奶奶不识字。
字迹很清秀,是圆珠笔写的,但有些地方已经晕开了。
我展开信纸。
“给我的乖孙女,然然:”
是妈妈的字迹。
信,是妈妈代笔写的。
“然然,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奶奶肯定已经不在了。你别哭,人老了,总有这一天。”
“奶奶这辈子,没什么大本事。没给你留下什么金山银山。这箱子里的钱,是奶奶一分一分攒下来的。”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奶奶就开始攒了。那时候卖一篮子菜,才挣几毛钱。后来帮你爸妈带你,他们给的生活费,我舍不得花,也都存了下来。一天存一块,有时候手头宽裕点,就存两块。”
“奶奶不识字,也不会去银行,就觉得这红彤彤的一块钱,最好看,最实在。想着给你攒个‘万元户’的嫁妆,让你嫁人的时候,腰杆能挺得直一点。”
“后来你长大了,嫁人了,过得也挺好。奶奶这钱,就一直没好意思拿出手。觉得太少了,拿不出手,怕你和你对象笑话我这个老婆子。”
“可这钱,放在我手里,我心里踏实。总觉得,万一哪天你需要了,奶奶还能帮衬你一把。”
“箱子里那个银镯子,是你爷爷留给我的念想。奶奶没什么值钱的东西,这个,就算是我和你爷爷,一起给你的。希望你和陈阳,能像我和你爷爷一样,好好的,过一辈子。”
“奶奶老了,脑子也不好使了。总是做梦,梦见年轻的时候。我怕我哪天走了,这事儿就忘了交代。所以让你妈,提前帮我写下来。”
“至于为什么跟你说是‘金子’……你小时候,不是最喜欢听奶奶讲金子的故事吗?奶奶就想啊,等我走了,就托个梦告诉你。让你来找,给你个念想。”
“这些钱,在奶奶心里,就是金子。是奶奶能给你的,最好的东西了。”
“我的然然,要好好的。”
信的最后,没有落款,只有一个用红印泥按下的、已经有些模糊的指印。
是奶奶的指印。
信不长。
我却看了很久很久。
等我抬起头的时候,脸上已经全是眼泪。
我再也控制不住,抱着那个装满了旧钱的箱子,嚎啕大哭。
哭得撕心裂肺。
陈阳默默地把我揽进怀里,他的眼圈也红了。
王阿姨站在一边,偷偷地抹着眼泪。
原来,这才是真相。
这不是一箱金子。
这比金子,贵重千倍,万倍。
这里面,是一个老人,用三十年的光阴,用无数个日日夜夜,用她粗糙的双手,为她的孙女,一点一点积攒起来的,最朴素,也最深沉的爱。
她甚至怕这份爱太过“寒酸”,拿不出手。
只能用一个善意的、带着童话色彩的谎言,把它包裹起来。
等到自己离开这个世界,再用一个梦,作为最后的钥匙,指引我来开启。
我哭了好久,直到嗓子都哑了。
陈阳一直陪着我,没说话,只是把我的手握得很紧。
天色,已经完全黑了。
院子里没有开灯,只有邻居家透出的微光,和天边一弯浅浅的月牙。
桂花树的影子,在地上摇曳,像一个温柔的拥抱。
“我们……把墙补上吧。”我终于止住了哭声,沙哑着说。
“好。”
陈阳找来水泥和沙,和了些泥,我们一起,把那个洞口重新砌好,又把表面抹平。
虽然手艺很糙,但总算恢复了原样。
院子里的那些坑,我们也一个个填平了。
做完这一切,我们俩都累得不行,直接坐在了院子里的台阶上。
谁也没说话。
我把那个银手镯,戴在了自己的手腕上。
尺寸刚刚好。
冰凉的触感,贴着我的皮肤,却让我觉得无比心安。
“这些钱,你打算怎么办?”陈-阳轻声问。
我看着怀里那个沉甸甸的箱子。
“我不知道。”
“要不,我们去银行问问,看能不能换成新钱?”
我摇了摇头。
“不换了。”
“就让它们这样吧。”
“这是奶奶留给我的‘金子’,一张都不能少。”
陈阳看着我,笑了。
“好,听你的。”
他顿了顿,又说:“以后,我们的孩子出生了,我们就告诉他,他的太奶奶,给他留了一箱子真正的‘金子’。”
我的眼泪又涌了上来,但这次,我笑了。
“嗯。”
我们没有在老家过夜。
收拾好东西,把那箱“金子”小心翼翼地放进后备箱,我们就连夜开车回了城。
回去的路上,我一直没睡。
我靠在车窗上,看着外面飞速倒退的夜景。
脑子里,全是奶奶的样子。
她给我梳小辫的样子,她给我做桂花糕的样子,她拿着蒲扇给我扇风的样子……
一幕一幕,那么清晰。
回到家,已经快半夜了。
我把那个木箱子,放在了我们的床头柜上。
没有再锁起来。
那天晚上,我睡得特别安稳。
我没有再梦见奶奶。
但我知道,她一直都在。
就在那个箱子里,在那个手镯里,在我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后来的日子,好像什么都没变,又好像什么都变了。
我和陈阳依旧每天上班,下班,还房贷。
为工作上的事烦心,为生活里的琐事争吵。
但我们好像,再也没有真正地红过脸。
每次我快要发火的时候,陈阳就会指指床头的那个木箱子。
我就会瞬间平静下来。
是啊。
还有什么,比“好好的,过一辈子”,更重要呢?
那箱钱,我们最终没有动。
它就成了我们家的一个“传家宝”。
有一次,我妈来我们家,看到了那个箱子。
我把整个故事讲给了她听。
她听完,沉默了很久。
然后她说:“你奶奶啊,就是这么个老太太。一辈子,心里想的,嘴上说的,总是不一样。”
“她嘴上嫌你爸没本事,可每次你爸回家,她都提前炖好了汤。”
“她嘴上说我乱花钱,可我买给她的新衣服,她都叠得整整齐齐,只有过年才舍得穿一次。”
“她就是这样,把所有的好,都藏在那些抱怨和唠叨后面了。”
我点点头。
是啊,她就是这样。
一个嘴硬心软,爱得深沉,却又笨拙得不知如何表达的老太太。
两年后,我怀孕了。
是个女儿。
在她出生前,我和陈阳做了一个决定。
我们把那一万多块钱,以奶奶的名义,捐给了一个帮助贫困地区女童上学的基金会。
捐款证书寄来的那天,我们把它和那封信,那个银手镯,一起放进了那个空了的木箱子里。
我们觉得,这可能是奶奶最希望看到的,这笔“金子”的用处。
让她的爱,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下去。
女儿出生后,我们给她取名叫“思莞”。
莞,是莞尔一笑的莞。
我希望她一辈子,都能笑得开心,活得坦荡。
等她再大一点,我会把这个箱子交给她。
我会告诉她,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很爱很爱我们的太奶奶。
她不会说好听的话,也没留下什么金山银山。
但她用尽了一生的力气,为我们留下了一箱子,全世界最最珍贵的“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