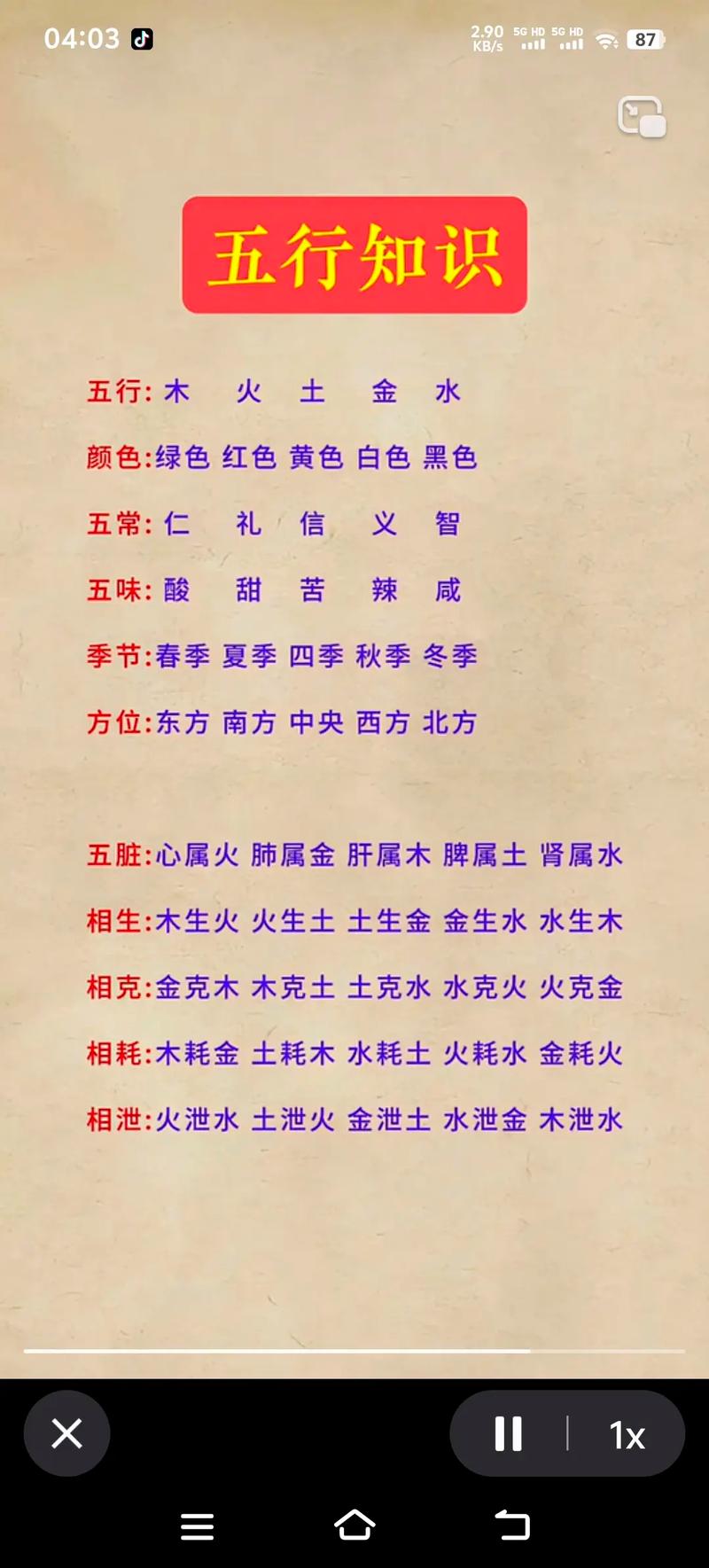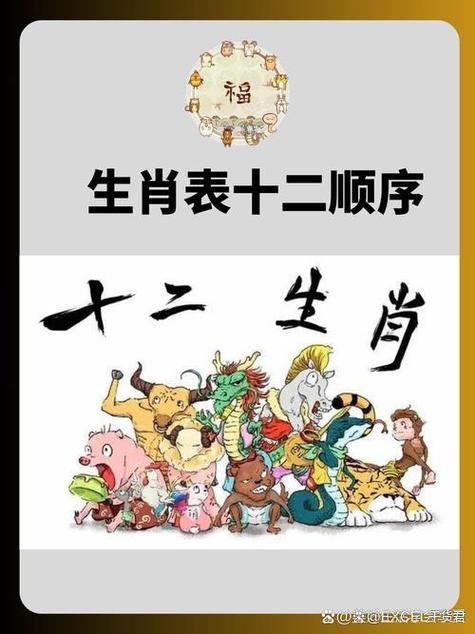不得了:爷爷去邻村摆摊,村长要他帮忙算命爷爷死活不肯:再算你活不过明天
01
我的爷爷,叫陈一山。
在我們王家庄以及附近十里八乡,你提这个名字可能没人知道,但你要是问“陈先生”,那上至八十岁的老人,下至刚会跑的孩童,都会一脸敬畏地指向我们家那座青瓦土坯的老屋。
爷爷不是教书先生,而是个算命先生。更准确地说,是看风水、算八字、解邪乎事的“阴阳先生”。
他这一辈子传下来的手艺,据说从我太爷爷的太爷爷那辈就开始了,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爷爷年轻时也曾名声大噪,据说几十里外的大户人家都曾八抬大轿来请过他。但随着年岁渐长,他的脾气也变得古怪起来,给自己立下了三不算的规矩:大奸大恶之徒不算,阳寿将尽之人不算,还有就是,关乎国运民生的大事,他一个字都不会透露。
所以,这些年爷爷基本是深居简出,整天就抱着他那个乌黑油亮的旱烟杆,坐在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下,一坐就是一下午,像一尊雕塑。只有当烟叶子抽完了,钱袋子也空了的时候,他才会慢悠悠地收拾起他的那套“吃饭的家伙”——一块洗得发白的蓝布、一筒老旧的竹签、还有一本被翻得卷了边的线装古书,带着我这个小跟屁虫,去附近的集市上摆个摊,赚点零花钱。
村里人都说,爷爷是有真本事的。谁家丢了牛,谁家孩子夜里哭闹不休,又或是谁家感觉撞见了不干净的东西,都会提着一包红糖或者几枚鸡蛋来找我爷爷。爷爷通常只是听他们说完,掐指一算,或者看一眼他们的面相,然后轻描淡写地说几句。说也奇怪,那些在旁人看来棘手的邪乎事,经他一点拨,大多都能迎刃而解。
当然,也有很多人觉得那不过是些巧合和心理安慰。在我看来,也确实如此。很多时候,爷爷指点的,不过是些人情世故的道理。比如张家丢了牛,爷爷会告诉他牛往东南方向去了,让他沿着河边找,顺便去下游的李家村问问。结果牛没找到,却发现是李家村的某个人偷了牛,两家吵了一架,最后村干部出面调解,牛还了回来。大家觉得是爷爷算得准,其实爷爷早就知道张家和李家那人有过节,不过是借着算命的由头,给他们指了个解决问题的方向。
所以,我对爷爷的本事,一直是半信半疑。直到那件事的发生,才让我彻底明白,爷爷那双看似浑浊的老眼里,看到的或许真的是我们凡人无法窥见的另一个世界。
02
那是一个夏末的清晨,天气有些沉闷,像是要下雨的样子。爷爷的烟叶子又见底了,他嘬着空烟杆,咂了咂嘴,对我招了招手。
“走,石头,跟爷爷赶集去。”
我一听就乐了。赶集意味着能看到各种热闹,还能央求爷爷给我买一串糖葫芦。我立刻放下手里的木头陀螺,屁颠屁颠地跟在爷爷身后。
这次我们去的不是镇上的大集,而是邻村“李家铺”自发形成的小集市。李家铺比我们王家庄要富裕一些,离得也近,翻过一道山梁就到了。
一路上,爷爷扛着他的那根标志性的黄竹竿,竿子上挑着个布包,里面是他算命的家当。我则跟在他身后,学着他的样子,双手背在身后,挺着小胸膛,一步一摇。
“爷爷,今天我们能早点回来吗?我还想去河里摸鱼呢。”我仰着头问。
“看生意。”爷爷的声音一如既往地平静,“要是开张得早,就早点回。”
到了李家铺的集市,果然已经人声鼎沸。卖菜的、卖自家编的竹筐的、还有耍猴的,把一条不宽的土路挤得满满当当。爷爷熟门熟路地在路边一棵大榕树下找了块空地,将蓝布铺在地上,把竹签筒和古书摆好,然后就掏出他的旱烟杆,盘腿坐下,闭目养神,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
很快,就有人认出了爷爷。
“哟,陈先生,您今儿个怎么有空来我们李家铺了?”一个卖豆腐的阿婆笑着打招呼。
爷爷睁开眼,点了点头,算是回应。
不一会儿,就有个妇人凑了过来,满脸愁容地问爷爷,她家孩子最近是不是中邪了,晚上总说胡话。爷爷让她报了孩子的生辰八字,然后从筒里抽了一根签,看了一眼,说:“没什么大事,回去用柚子叶煮水给孩子洗个澡,让他晚上早点睡,别在外面疯跑就行了。”
妇人千恩万谢地留下两个鸡蛋,走了。
我知道,这又是爷爷的“老套路”。小孩子精力旺盛,白天玩野了,晚上自然睡不安稳。柚子叶洗澡不过是个仪式,关键是让大人管束好孩子。
就这样,一上午过去了,爷爷的生意不好不坏,布包里多了几个鸡蛋和几毛钱。眼看快到中午,太阳被云层遮住,天色更加阴沉,爷爷估摸着要下雨,正准备收摊,一个洪亮又带着几分蛮横的声音从人群外传了进来。
“都让让,都让让!挡着路了!”
03
人群像被劈开的水波一样向两边散开,一个身材肥硕的中年男人走了过来。他穿着一身当时在农村还很罕见的的确良衬衫,肚子把衬衫撑得鼓鼓的,腰间系着一根牛皮带,上面挂着一大串钥匙,走起路来叮当作响。他脸上油光满面,一颗大金牙在阴沉的天色下格外显眼。
我认识他,他就是李家铺的村长,王老财。据说他早年在外面倒腾过木材,赚了些钱,回到村里后,靠着手里的钱和一些人脉当上了村长。在李家铺,他说话向来一言九鼎,谁都不敢得罪。
王老财径直走到我爷爷的摊子前,居高临下地瞥了一眼地上的东西,扯着嗓子说:“你就是王家庄那个算命的陈先生?”
他的语气里没有丝毫尊敬,倒像是在审问犯人。
爷爷缓缓睁开眼睛,浑浊的目光在他脸上停留了片刻,不咸不淡地“嗯”了一声。
“听说你算得挺准的?”王老财咧嘴一笑,露出了他的大金牙,“来,给我也算一卦,算算我最近的财运怎么样?要是算得准,这个,就是你的了!”
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崭新的大团结(十元纸币),在指间弹了弹,动作充满了炫耀和轻蔑。在那个年代,十块钱对于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足够买好几斤猪肉,给我添一件新衣裳了。
周围的村民都围了过来看热闹,对着王老财指指点点,又对我爷爷投来好奇的目光。
我以为爷爷会像对待其他客人一样,让他报上生辰八字。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爷爷只是静静地看着王老财,看了足足有半分钟,然后摇了摇头,慢慢说道:“你的命,我算不了。”
这话一出,空气仿佛都凝固了。
王老财脸上的笑容僵住了,他把那张十元钱收了回去,脸色沉了下来:“怎么?嫌少?还是看不起我王某人?”
“都不是。”爷爷的语气依旧平静,“我说了,你的命,我算不了,也算不起。村长请回吧。”
“嘿!我今天还就非要你算了!”王老财的蛮横劲上来了,他往前踏了一步,几乎要踩到爷爷的卦摊,“今天你要是不给我算,就别想走出我们李家铺!”
周围的村民开始小声议论起来,有人劝王老财算了,说陈先生脾气怪,别跟他一般见识。但王老财正在气头上,哪里听得进去。
我有些害怕,紧紧地攥住了爷爷的衣角。爷爷却依旧稳如泰山,他抬起头,那双平时总是半眯着的眼睛此刻完全睁开了,目光像两把锋利的刀子,直直地刺向王老财。
04

爷爷盯着王老财的脸,一字一顿地说道:“王村长,不是我不给你算,是你的命,我算不起。我这双招子,看的是阴阳,算的是生死。有些人的命,沾了不该沾的东西,命数早就乱了,谁算谁倒霉。”
他的声音不大,但在嘈杂的集市上却清晰地传到了每个人的耳朵里。
王老财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他似乎被“不该沾的东西”这几个字刺痛了,勃然大怒道:“你个老神棍!胡说八道些什么!我看你就是个骗子!今天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不知道我王老财的厉害!”
说着,他抬起脚,一脚就踹翻了爷爷的摊子。
竹签筒滚落在地,里面的竹签撒了一地。那本泛黄的古书也掉进了泥水里。
我吓得大叫一声,赶紧扑过去捡书。爷爷却一把拉住了我,他慢慢地从地上站起来,身形有些佝偻,但腰板却挺得笔直。他没有去看地上的狼藉,只是冷冷地看着王老DUMP,那眼神,是我从未见过的冰冷和锐利。
“好,好,好。”爷爷连说了三个“好”字,然后说出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的话。
“再算下去,你就活不过明天了。”
这句话仿佛一道惊雷,在人群中炸开。所有人都惊愕地看着我爷爷,又看看脸色由青转白,由白转紫的王老财。
王老财像是被掐住了脖子的公鸡,半天没说出话来。他指着爷爷,手指都在发抖,“你……你敢咒我?”
“这不是咒,”爷爷的声音里没有一丝波澜,“这是实话。你的印堂发黑,凶兆已现,本就命悬一线。你若安分守己,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你若再执迷不悟,惊动了不该惊动的东西,神仙也救不了你。”
“滚!你给我滚!”王老财终于爆发了,他指着村口的方向,歇斯底里地吼道,“马上给我滚出李家铺!以后再也别让我看见你!”
爷爷没有再多说一句话,他拉着我的手,转身就走。连地上的东西都不要了。
我们默默地走着,身后是王老财的叫骂声和村民们的议论声。走出很远,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只见王老财还站在原地,脸色阴沉得可怕。
我心里又怕又急,问爷爷:“爷爷,我们的东西都不要了吗?那本书……”
“不要了。”爷爷头也不回地说。
“爷爷,你为什么不给他算啊?你还说他活不过明天,是真的吗?他会死吗?”我追问道。
爷爷没有回答我,只是阴沉着脸,脚步走得更快了。
就在我们快要走出李家铺村口的时候,爷爷却突然停下了脚步。他转过身,朝着集市的方向,用不大不小,却足以让附近的人听见的声音喊了一句:
“王村长,看在乡里乡亲的份上,我多句嘴。这几天,把你家那条大狼狗拴好了,千万别让它跑出来。”
说完这句莫名其妙的话,爷爷不再停留,拉着我,头也不回地翻过了山梁,往我们王家庄走去。一路上,任凭我怎么问,他都一言不发,只是手里的旱烟杆,被他捏得咯吱作响。
我看着爷爷那张比天色还要阴沉的侧脸,心里第一次涌起一股彻骨的寒意。
05
回到家后,接下来的几天,日子过得异常平静。
爷爷把从李家铺带回来的几个鸡蛋煮给了我吃,自己则又开始坐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一言不发地抽着不知道从哪里又摸出来的零星烟叶。他再也没有提过王老财,也没有提过那天在集市上发生的事,就好像那只是一场寻常的赶集。
可我知道,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爷爷的沉默比任何时候都要沉重,他看我的眼神里,也多了一丝我读不懂的复杂情绪,像是担忧,又像是怜悯。
村里渐渐也传来了一些风言风语,说王家庄的陈先生把李家铺的村长给得罪了,还咒人家活不过明天。有人说爷爷是吹牛,有人说爷爷是真有本事,把王老财的丑事给看穿了,才惹得他恼羞成怒。
我也曾悄悄问过村里去李家铺走亲戚的二牛叔,王老财怎么样了。二牛叔说,好着呢,天天在村里骂骂咧咧的,说早晚要找人来拆了我爷爷的“封建迷信”摊子。
听到这些,我心里的一块石头似乎落了地,但另一块石头,却悬得更高了。尤其是爷爷那句关于“拴好狗”的嘱咐,像一根刺,扎在我的心里,百思不得其解。王老财的生死,和他家的狗有什么关系?
时间就这样,在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涌动的氛围中,悄然滑过了五天。
第五天,天刚蒙蒙亮,鸡才叫过头遍。我像往常一样,睡眼惺忪地提着一小簸箕米糠,走到院子里喂那几只老母鸡。清晨的空气带着一丝凉意,吸进肺里很舒服。我们家的小院很安静,只能听到母鸡们“咯咯咯”的啄米声。
就在我刚把米糠撒在地上,准备回屋洗把脸的时候,院子那扇破旧的木门,突然被人敲响了。
“咚、咚、咚。”
敲门声沉重而急促,一点也不像平日里来串门的邻居。我心里“咯噔”一下,一种不祥的预感瞬间涌了上来。
我跑过去,踮起脚,费力地拉开门栓。
门外站着两个人,他们的穿着让我瞬间清醒了过来——是两名穿着制服的警察。他们的表情异常严肃,帽檐压得很低,眼神锐利地扫了一眼院子。
其中一个年纪稍长的警察弯下腰,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温和一些,问我:“小朋友,请问,陈一山老先生是在这里住吗?”
我点了点头,有些紧张地回答:“我爷爷在屋里。警察叔叔,是……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两个警察对视了一眼,那个年轻一点的似乎想说什么,但被年长的用眼神制止了。
年长的警察沉默了一下,似乎在斟酌用词,最后,他深吸了一口气,沉声说道:
“李家铺的村长王老财,他家……昨天晚上一家老小,全被人给灭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