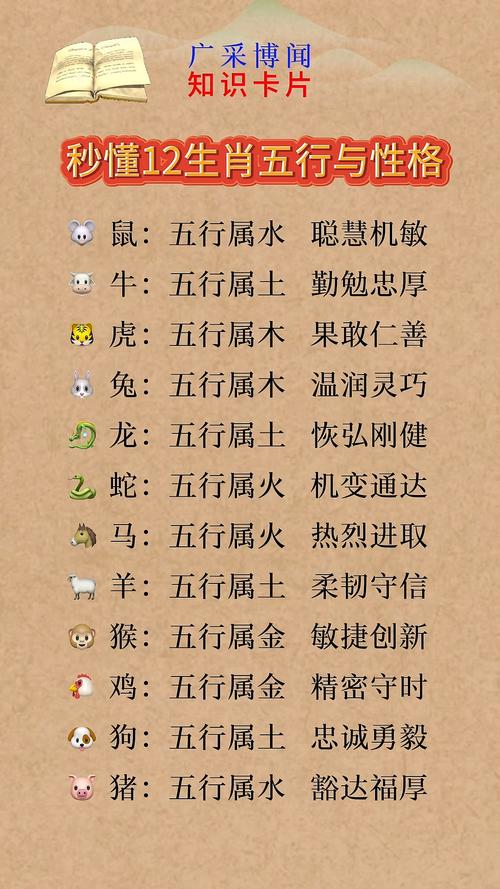春节前夕罗萱妈妈拒绝与女儿共度,却热心采买年货为家人准备
眼下,春节在即,罗萱妈妈拒绝了和女儿一起过年的邀请,但依然热心采买年货。
乘坐武汉578路公交车,途经18站,直至终点站武昌汉阳门,罗萱妈妈便可到达一家连锁大型超市。家门口的超市近在咫尺,但她嫌贵。罗萱爸爸爱吃的港饼楼下超市卖13.8元,那家大超市只要6块。她买了港饼、大米饼、巧克力和点心。港饼被放入罗萱爸爸遗像前的供品盒里,大米饼、巧克力和点心则是两个外孙爱吃的食物。
她和罗萱虽不言明,但都倒数着春节的来临。因为除夕一到,再过十天,就是罗萱爸爸的一周年忌日。
冬日的暖阳下,罗萱爸妈楼下的小广场上,一位老人来回三四趟,将一床床被单抱上一个铝制铁架,挂好,捋平。一对中年男女在旁,一个舞剑,一个耍太极柔力球,各自开着嘹亮的音乐,却彼此不以为扰。
时间在这里无声柔软地滑过。就在这个小广场上,罗萱爸爸曾教外孙学会了骑自行车,闲暇时光,他总带孙子孙女来这儿追逐嬉闹。
如今,孩子们依旧常来小广场玩耍,可身后再也没了外公。
不久前,女儿问她爷爷(孩子们一直称呼外公为“爷爷”)新冠怎么了?罗萱平静地向女儿解释:爷爷的肺部被病毒侵蚀了。肺部帮我们呼吸,把氧气送到血液,肺不能动,空气就进不了身体,人没了氧气,就运转不了了。
不只两个孩子,这一年,罗萱也一次次地思考着什么是人生?什么是死亡?死亡到底意味着什么?
2020年3月25日,罗萱拿着单位开具的出工证明奔跑着出小区。在狂风大雨中,她的内心狂跳不止。
虽然仅隔1公里,因为武汉的“封控”政策,她和妈妈有60余天没见面了。一路上,她想象着自己如何扑上前紧紧抱住妈妈,但走进家门的那一刻,她站在原地动弹不了。
她不可自抑地落泪,看着母亲故意忙碌的身影,罗萱终于说出那句早在24天前就该说的话,“爸爸走了”。
母亲戴着口罩,隔着一米远坐着,不动声色,平静如水。见她嚎啕不已,母亲淡淡说道,“别哭了,眼睛哭坏了”。
母亲问罗萱,“你爸爸是不是20几号走的?那些天,我总梦到有人在床头坐着,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母亲还说,那时她在电视新闻里看到一个片段,医生指着一个病人说道,“这人病得太严重,连抢救的必要都没有了”。
她坚持认为那是自己的丈夫,“那件袄子和大大的裤子都跟你爸的一模一样,真的很像”。看着电视,她坐在沙发上,自言自语道,“你要是真的不行,我就把你送回老家”。说完,她打了一个喷嚏。
罗萱没有告诉母亲,就在那几天,她也做过一个梦。那是一个更具象的梦。
梦中,父亲穿着离家时的衣服,两手空空回来了。罗萱问父亲,你怎么回来了,谁把你送回来的?父亲答:姑姑把我送回来的。一旁的母亲只是哭,靠在客厅的窗户不走近来。
罗萱知道父亲已经去世了,父亲口中的姑姑也已逝世多年。父亲提出要洗个澡。他一边洗澡,罗萱丈夫的手机一边播放着一个故事,故事里说着“一个人如果心愿未了,魂魄会一直在世间飘荡”。
罗萱责怪着丈夫为什么播这么大声音,却突然看见父亲裹着一条红色被子站在灶台边,出神地向外张望。她看不到爸爸的脸,只看见鼻子。
她从梦中惊醒,问自己是不是忘了父亲的头七,才发现离父亲去世刚过去两天。
此后,她再也没有梦见父亲。这成为她有关父亲的唯一一个梦,也成为父亲对她最后的告别。
去罗萱父母家的路上
这一年,罗萱一再和母亲复盘爸爸的离去。她才发现,父亲早在就医前两周就有不适,却未告诉她。父亲最后一次去罗萱家是戴着口罩的,否则,罗萱夫妇和正上小学的一双儿女将可能受到病毒的侵袭。
罗萱爸爸在2020年1月26日开始出现低烧、呕吐、腹泻的症状,直至2月5日才得以入院。期间,他已确诊患有新冠肺炎,先后辗转武汉六家大大小小的医院,却都未能获得一席床位。
罗萱父母历经深夜通宵排队,罗萱曾在政府部门求助热线电话中失声痛哭。要不是罗萱爸爸的同事将罗萱直接拉进单位同事群,罗萱爸爸也不会得到他们的帮助,顺利进入武汉市协和医院西院接受治疗。
为了向叔叔阿姨们汇报进展并道谢,罗萱特意嘱咐丈夫给爸爸拍张照。照片定格了父亲在亲人们眼中最后的样子——一身黑衣,一顶皮帽,一个黑色皮箱,坐在救护车内。
行李箱里,是罗萱塞入的苹果、牛奶、衣服、自己儿女的相片,还有一本贾平凹的《自在独行》。
入院的前八天,罗萱跟父亲打过视频电话。父亲喘得很厉害,医院让送过两次免疫球蛋白。一次丈夫向保安求情送到了病区,后来一次,保安坚决不放,护士一直催促,最终丈夫把东西放在了运送遗体的电梯里,护士在楼上等候取出。
2月13日,父亲插上呼吸机后,彻底没了音讯。罗萱一边担心,一边劝慰自己: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
奇迹没有发生。2月21日上午八点半,那个电话终于来了。医院医生说,你爸爸不行了。罗萱哀求对方,能不能再抢救一下。半小时后,她再次接到电话,“人走了”。
父亲去世后,带去的物什都被医院统一处理掉,回到罗萱手中的只剩父亲的手机、身份证、医保卡和一张银行卡。在病区冰箱内,还留存着几瓶父亲剩下的免疫球蛋白,罗萱不要了,任医院处理。
在罗萱告知父亲的死讯后,母亲平静地做出了两个决定:一是把父亲葬回广西玉林老家,与父母兄妹有个伴;二是给老家亲人一笔钱,算是父亲对他们最后的心意。
为了找出银行卡、存折、股票的密码,罗萱不得不闯进了父亲的一件件遗物里。
这是她第一次认真地坐定在父亲书桌的抽屉前。翻开抽屉,她看到了父亲的一个个笔记本。那些笔记本有着久远的历史,记载着30余年前父亲当雷达兵时记录的繁杂数据与党课笔记。在一张张汇款单里,她发现了父亲数十年来未曾倾吐的秘密。
少则几千,多则几万,每张汇款单的收款方均是父亲在广西农村老家的弟兄。最近的一次在2019年12月,父亲向罗萱的九叔汇去了一万元。
罗萱把这些汇款单拿给母亲看,母亲没有怨恨父亲,只是恍然大悟地说道,“怪不得他总是一块两块都舍不得,原来他是渡船,不只要渡自己家、女儿家,还要顾兄弟姊妹家”。
最终,罗萱在一个存折里,找到了父亲常置的密码。在银行柜台前,母亲坐着,她站在一旁。她犹豫了一下,将死亡证明对折着递进了玻璃窗内——她不愿母亲看到那张纸,那样直视父亲的死亡。
几分钟后,母亲说不舒服,站到了银行门外透气。于是,罗萱坐在了柜台前。很快,她如坐针毡,想立即逃离。她在银行开过户,取过钱,却是第一次为已逝的父亲办理业务。
她试图告诉自己,爸爸还在医院,只是住院没有回来。但转念,现实就无情地直诉真相。她的心,好疼。
很快,她会明白,银行卡“销户”只是一个开始。她必须亲自让父亲在这个真实的世界逐渐脱退,直至最终消失。
午后,罗萱父母居住的小区门口前,写有“民政救灾”的蓝色帐篷内传来阵阵防疫知识的广播声。一把中年男声字正腔圆地说着“做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从这里出发,往西走数十米,道路右侧的墙上会出现一张红字黄底的标牌,上面写着“零感染小区”,那里便是罗萱居住的地方。
继续向前,道路沿坡而上,路的一侧有水果摊、电焊铺、报刊亭,另一侧是几栋待拆建筑。走到路口,鳞次栉比的老旧小区就被甩在了脑后,眼前都是高楼大厦与繁忙大道。
再往前,就到了武汉沙湖公园——罗萱父亲在世时,父母两人总是散步至此。他们常常带着孩子们在公园的沙坑里嬉戏,还用湖边尖尖长长的叶子佯装钓鱼。罗萱爸爸不在后,罗萱母亲每天仍独自走在这条路上,造访同一片公园湖泊。
罗爸爸在世时常带孙子在沙湖边用这种长叶钓鱼。
罗萱妈妈性子很淡,这些年,爸爸包揽了做饭等家务,既是妈妈的丈夫,也是她唯一亲近的朋友。他们每天一起散步,乘坐新开通的地铁线探访未去过的地方,爸爸做饭时,妈妈会在一旁陪着谈天。
爸爸去世后,罗萱很担心母亲,但母亲总说忙,要学做饭,要料理家务。她像一个重新成长的女孩,学习着怎样在一蔬一菜中让失序的生活重新回到正轨。她告诉罗萱,每天吃完早饭会去沙湖走走,回来就得准备午饭,如此往复,光一日三餐就让自己忙碌不已。
母亲不愿罗萱与孩子们去看她。如果罗萱坚持,她会提前洗晒衣物,并全房消毒。她本就有肺不张的旧病,加之与丈夫密切接触,她一直将自己视作携带新冠病毒的潜在传播源。
直至2020年5月武汉实行全民核酸检测,罗萱妈妈才得到一个确凿的结论:她的核酸检测呈阴性,血清抗体呈阳性,这意味她曾被新冠病毒所感染,如今已自愈。这之后,母女俩在家相对而坐时才摘下口罩。
但罗萱仍能感受到母亲的疏远。过去,母亲几乎每周帮忙来打扫卫生,常和父亲在家陪孩子玩耍。现在,母亲鲜少去罗萱家,即使去送东西,也只到门口,不愿进屋。
如此临近的距离,他们却开始习惯以视频的方式见面。

8月时,一只孔雀误入了小区。连续几天,母亲都在孔雀的叫声中醒来。她洋溢着少有的喜悦,在罗萱的指导下,学会了在视频中用后置镜头给两个外孙看孔雀。三天后,孔雀离开了,母亲有些不习惯,嗔怪着孔雀打乱了她的生活规律。
夏天快要结束时,罗萱发现,母亲开始变得健忘。她会忘了买菜付钱,忘了罗萱教过她用支付宝转账,忘了曾有人来家里修过有线电视。她告诉罗萱,这一年的生活,始终像在做梦。
她半宿半宿的睡不着觉,脚上长出一圈红疙瘩,头上出现一块块斑秃。罗萱心疼却无他法,只能为母亲购买各类不知是否有功用的维生素。
到了11月,母亲终于答应让罗萱帮她理发。她说,“这个头发是你爸爸给剪的嘛,我本来想一年后再剪的,不过现在脱发这么厉害,剪了吧。”
过往很多年,母亲都是齐耳短发,头发长了,父亲就帮她修理。父亲走后,母亲的头发一点点长长,直至披肩。
那是一个周末的早晨。罗萱拿起父亲不知使用过多少次的理发工具,开始了工作。捧着母亲稀疏单薄的头发,她心里泛着苦味,母亲曾引以为傲的厚重头发如今抓在手中,已没什么分量。
罗宣常给儿女俩理发,为母亲理发的心境却有些不同。她将母亲的头发轻轻打湿,一缕缕分好,用剪刀利落地把长发剪短,对称两边统一长短,再细细地剪短脸颊边的鬓发。
洗完,吹干,母亲又变回了过去的齐耳短发,那抹灰色的头发显得更单薄了。罗萱和父亲谁理得更好?母亲未评价,罗萱也没有问。就这样,女儿悄无声息地接过了父亲延续多年的一项重要职责。
无论如何逃避拖延,时间终于还是指向了10月。从母女俩决定将骨灰葬回广西,她们就倒数着这一天的来临。起初,因为“封城”,她们可以将此事一拖再拖,到老家亲戚请人算好日子,一切都变得不可回避。
去殡仪馆领骨灰的路上,罗萱妈妈一路念叨着,“我们去医院的时候路过这里”,“那么大个活人拎着行李箱去看病,回来就这么一个小盒子”……她情绪低落,却依旧没有落泪。
因为距离去广西尚有时日,他们将骨灰暂存在了小区所属区域的殡仪馆。期间,罗萱接到社区电话,问可否先登记父亲骨灰已下葬,系统需要这个“钩”,才算了结父亲的丧葬事宜。罗萱答应了。
临近出发的日期,因为自家轿车是红色,罗萱和丈夫提前选定了待租的车辆,没有任何犹豫,大家就达成一致——罗萱夫妇前往广西,母亲留下照料孩子。
10月24日,罗萱和丈夫出发了。父亲的遗像裹着布,与像屋顶般的骨灰盒,系着安全带,端正地被放置在汽车后座。
罗萱夫妇驾车进入广西境内
罗萱回老家的次数屈指可数,开车回去更是头一回。她知道,年少就离家从军的父亲对故土有着深厚的眷顾,退休后的第一年便回去住了两个月,罗萱二宝出生后,全家又一同回去住了一个月。罗萱母亲因为知青下乡的经历,不愿再回农村,因此罗萱爸爸即使退休后也依然定居武汉,只能偶回故乡。
这一次,父亲终于可以回到故土长眠。一路,天空湛蓝,白云疏落。罗萱和父亲的骨灰以相同的视角看着一座座小山在平原上拔地而起,看着故乡的山水在窗边不断地退去,看着九叔家的两棵大树由远及近。
26日,抵达老家村落后,罗萱就前去了宗亲所在的墓地。墓地在一座厂房背后,那里曾是一片竹林,罗萱幼时曾在那里玩过。
红烛、纸钱、全鸡、酒杯摆在墓前,罗萱打着黑伞,抱着沉重的骨灰盒,咀嚼着与父亲的告别。同天,罗萱三伯的墓也迁至于此。叔婶们稀松平常地谈着天,烧一栋纸作的二层楼别墅时,笑着说道,“让他们自己分去”。罗萱和丈夫成为了那个时空里格格不入的悲伤者。
随着罗萱、丈夫和九叔每人反手撒下三把土后,罗萱父亲真正落叶归根了。一盘直径半人高的鞭炮发出巨响,一阵浓烟终于模糊了罗萱的双眼。
上世纪九十年代,罗萱一家终于搬到了父母现在的住处。当时全家开心了很久。此前,他们搬过数次家,最后一次住在母亲所在电路板厂的租住地。
那是一间大教室,桌椅占据了四分之一的空间,一下雨屋檐就漏水,总得在天晴时把家具拿出去晾晒。
当车驶进新住处时,罗萱妈妈的心凉了半截。尽管那里是所在区域第一个规模小区,但周边全是土坡,一片荒凉,与之前毗邻汉正街的住处形成鲜明对比。
如今,因为密集分布省府机构、坐拥武汉多所名校,这里已是寸土寸金的地方。但罗萱妈妈依然对这所房子颇有微词,不只因为它小,还因楼栋朝向而导致的阳光稀少,使每个冬天都冻得难熬。
父亲在世时,全家在武汉远城区买了一所大且阳光充裕的房子。还未装修入住,罗萱爸爸先走了。
罗萱提出要不把现居的房子卖了,母亲坚决不肯。她不愿再离开这所房子。当罗萱因亲人的提醒,向母亲提出过户时写自己的名字,避免以后再从母亲过户给她的麻烦,母亲突然情绪激动,质问罗萱,“我连一个屈身之所都没有了吗?你们连我睡觉的地方都要拿走吗?”
提出房产过户后的几天,罗萱妈妈发来微信,说自己想多了,当时补存折都大费周章,房产确实应该写罗萱的名字,可以省去很多麻烦。
但几天后,坐在房管局办事大厅,罗萱妈妈看着公证书再次崩溃。她恍恍惚惚地问罗萱:“这是说,房产证上就只写你一个人的名字了?”罗萱愣住了,机械地点了点头。妈妈立即爆发了,在大厅大声喊道,“你太狠了吧?连我这个老太婆唯一居住的地方都要拿过去?我以后住大街上吗?”
罗萱立即宽慰母亲,说如果不能写两个人名字就不办了。到了窗口,工作人员告诉母女俩,可以同时写上她们的名字。办完事,母亲松弛了下来,一脸轻松地告诉罗萱,“你忘记了,当时公证人员说可以写两个人的名字的”。
罗萱父母所在的小区广场
办完房产过户,罗萱不得不面对父亲离去的最后一道手续——销户。
之前,她总是困于与父亲死亡相关的一件件繁杂的手续与流程,这一刻,她突然体悟到这些琐事背后的意义,它们以这样的方式消解活人的精力,也以此来弱化悲伤,并通过这一桩桩具体的事让活着的人与逝去的人产生着最后真实的联系。
这是一场漫长的告别。而去派出所办理销户,意味着生者真正的消失。所以,这一年,尽管罗萱接到了无数次派出所催促销户的电话,她仍然一再寻找理由选择推延。
处理银行卡、办理丧葬事宜、更换房产归属……一切都结束了,没有理由再拖延了。
2020年12月28日,罗萱终于带着户口本和父亲的身份证走进了派出所。所有流程比她想象中简单太多,仅仅几分钟后,手续就已办妥。
户口本上,父亲的那一页还在,只是盖上了“注销”的戳印。罗萱打开手机搜索,父亲的社保信息在当天已无法查到。
父亲真的消失了。
从父亲开始求医到最终逝世,这个叫“新冠”的病毒仅用了25天,就夺走了这个陪伴了她三十余年的生命。
她像患上了某种后遗症,执着地去看疫情相关的影视剧、纪录片,不为别的,只想知道父亲与他们分离的那16天里,在医院究竟独自面对着什么。她在QQ空间、日记本上,写下大段大段冗长的话语,只想让生活与过往以另一种方式暂时凝固。
她的体内仿佛有两个自己。一个自己如往常般上班、送娃、下班、接娃,乐观开朗,而另一个自己永远停顿在了某个地方,一想到父亲就难以自抑情绪,仿佛一切都在梦境。她不明白,走在大街上,有那么多人,有那么多父亲、母亲、儿子、女儿,为什么偏偏她的父亲,成为了一个“确诊人数”数据中的渺小组成部分。
12月5日,罗萱夫妇带着女儿去武汉中南医院看病。汽车平稳驶向前方,罗萱的哭泣声却由小及大。末了,她才喃喃地对丈夫说,“爸爸当时也走过这条路去医院啊”。事实上,因为她要照顾孩子,父亲的求医路上始终由丈夫和母亲陪伴。她与父亲的最后一面永远停留在了2020年除夕。画面里,父亲戴着口罩站在架子上查看电闸,两个孙子“爷爷爷爷”地围着铁架呼唤着他。
她曾搜肠刮肚想思考“父亲最让她感动的事是什么?”,却无果。后来,她才突然想起,小学时,自己因为感冒鼻塞无法入睡,父亲每天给她的鼻子、头部做按摩,直至感冒痊愈后,还坚持了近一年。
除开这个显性的事件,她与父亲的相处竟然那样平淡,她找不出父女情深的更多例证。
但在父母家与她的小家里,一个个普通无奇的陈设都为父亲的存在提供着无声却有力的证言。父母家的衣柜、橱柜、鞋柜都由父亲亲手打造,罗萱家宽大的工作台花费了罗萱爸爸两个月的时间,他为其精心打造了两个收纳柜,推着自行车一趟趟从自家驮到了罗萱家。还有阳台铁架上的朝天椒,到如今依然释放着鲜艳的活力。
罗萱父亲种下的辣椒依然高产
一个傍晚,罗萱妈妈在厨房摘菜,罗萱靠在门边。妈妈告诉罗萱,最近又翻出父亲的两个存折,然后,她突然说道,“夫妻的缘分是上辈子就定好的,是几年就几年,缘分到了,只有两种结果,要么离婚,要么一方死亡。”说完,她们都久久不语。
年关将至,除夕越来越近。因为今年是罗萱爸爸的“新年”,依照传统他们不能在春节期间去别家拜年。然而,一家五口的团年饭也被罗萱妈妈拒绝了。这个春节,让罗萱无所期待。
她将不会再品尝到爸爸最拿手的白斩鸡和扣肉,还有过年过节必包的大粽子,也无法再体会什么是“团圆”。
2020年2月21日,得知父亲死讯时,罗萱正和孩子一起躺在床上。听到她的抽泣,儿子问她,爷爷怎么了?她哽咽着小声憋出四个字:爷爷死了。年幼的女儿继续追问,爷爷去哪儿了?她不可抑制地痛哭起来,无法再言语。
(文中罗萱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