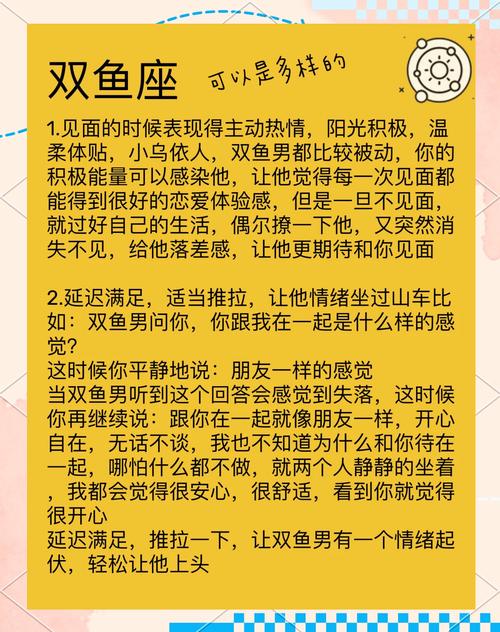【文/姜福军】苦命的三叔(小说)
苦命的三叔(小说)
文/姜福军
三叔是在后半夜小解时从坑上摔下来的,经这突然一摔,立不起身了,这昨天还好好的么,出了怪事了。三叔使劲爬到门前,在门缝旁大声哭喊着月兰的名字,因为月兰家离他家最近,半夜三更的,喊了好长时间,喉咙都喊哑了,月兰隐隐约约所见了,那嚎声是绝望,是无助,是对尘世的留恋。等月兰来拨开门闩,三叔已是有气无力了,身软如泥,好不容易搀扶到坑上,盖好被子,寻着三叔的老年机给三婶打电话时,三婶手机早关了。
三叔命苦呀!老婆常年在西安打工,在饭店洗盘子刷碗,这都干几年了。三叔才五十八九,还没过六十岁,患的病是脑梗,好几年了。但能吃能喝能跑能干点杂活,生活能自理,药从来没离过囗,从没摔倒过,咋就一时半刻摔倒了,严重了,腿一下子不听使唤了,手乱抖乱抓,胡言乱语。月兰给三叔倒了些水,问:有药吗?三叔哆哆嗦嗦地说:有,在抽屉里。照看三叔喝了道:先将就着,天明了我再打电话。
天一亮八点多月兰才打通了三婶的电话,三婶说:他是老毛病又犯了,几年了,你是知道的,脑子有病,脑梗高血压,整天喝药哩,摔倒可是头一回,知道了,我下午就回来。
西安距上洛县草房子村不是很远,也就是三个多小时的车程,现在西安到各县都通了高速公路,比以前方便多了,三婶从请假到收拾东西再从南郊坐公交车到省城汽车站买票上车,急急匆匆的,中午一点多就到家了。村上在家的人都来帮忙了,三婶忙前忙后的,也顾不得谢月兰,先急急火火把三叔拉到街上卫生院,卫生院简单诊断了一下,负责人叫不敢耽搁,赶快转县医院,三婶有雇车拉到县医院,等办完入院手续,睡到病床上挂上吊瓶,就折腾到下午四,五点了。
医生诊断是脑梗导致脑中风,病情加重,身体半边瘫,肢体瘫,走路不稳,无力,口歪眼斜,大小便失禁,属高危患者,须住院观察治疗一段时间,使病情趋于平稳,但不能保证有无意外,叫三婶签了字。治疗一个月后,谢天谢地,钱没白花,能下床慢慢走路了,但需人陪着搀扶,手还颤,挪步时右腿还向前一撇一撇的,嘴里独说独念,哀声叹气,悲观绝望。尤其是三叔见了熟人就哭诉:好好的人咋得这病吗?我是上辈子杀人了放火了,咋遭这孽了?这活着拖累人有啥活头吗?眼泪一把鼻涕一把,口水乱流。三叔知道自己成了家里的累赘,才说这样的话。熟人就宽慰道:人吃五谷得百病,好好看,一定能看好的。但熟人背过脸去都不免眼睛发酸,心生怜悯,是瞎瞎病,再多的钱也治不好,况且三叔家还是个穷户。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人呀!谁都不是神仙,谁都无法预料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
这一个月里,三婶伺候三叔真不容易啊!要搀扶上厕所大小便,要到外边买吃买喝提上来给一勺一勺喂,半夜病情加重了要叫医生。她就圪蹴在三叔病床那头,衣服也没脱,夜晚凑合着睡,没睡好没吃好,人一下子瘦了一圈。少来夫妻老来伴,她也知道自已常年打工挣钱,亏欠了男人,所以她尽自己的能力,配合男人和医生,心想好转了就拉回去调养,虽然现在有合疗,但要先垫钱,住的时间长,花费大,也不是办法呀。
一个半月以后,己经花了七八万元了,这把三叔攒的那一点老底子花完了,这七八万元是年轻时下苦力挣下的血汗钱,是从牙缝里省下的,年轻时挣钱年老看病,这下给自己派上了用场,至于给儿子说媳妇买房,那只是奢望了。好在三婶打工还存了四五万元又取出来给医院交了,住院治疗两个月后实在没钱了,山穷水尽了,三叔也能自己慢慢下床活动走路了,不需要人搀扶了。在一个早上三婶叫医院给三叔办理了出院手续,医生给带了药,在药合上写了服用剂量,药好多,名字怪异,阿司匹林肠溶片,阿替普酶,尿激酶,氯吡格雷,达比加群,利伐沙班,阿加曲班等等…整整装了二大袋子,雇车又把三叔拉回草房村了。
这天西安饭店老板给三婶打电话叫上班,三婶说:家里缺人手,伺候老汉病好了就来了。老板说:你还要拖到啥时候?不来,你那半年多工钱甭要了。因三婶那天走的急,工资根本没结,这四五万元,还是以前干活攒下的。她不由得给远在广东打工的儿子打了电话,叫赶紧回来替换自己,多一个人多一个帮手。她开始没打,怕影响或吓着儿子,实在撑不住了,才给儿子打电话了。
村上人都来看望三叔了,东家两包糖,西家几斤鸡蛋,东家一箱奶,南家一包点心。这个风俗在草房子村已经沿袭很久很久了。谁家人病了住院回来了或遭了大难大灾,村上人都要上家看望的,礼或多或少,或轻或重,能到家里来,主家都高兴,关健是不空手就行,和病人拉拉家常,说些宽心话安抚情绪比什么都好。这几年,谁家有个红白喜事,村上人户户都去帮忙,全家吃饭都在本家,洗洗碗洗洗菜,搬桌子搬板凳,倒茶发烟,招呼来客,平常不太见面的都见面了,唠唠嗑,打打牌,划拳喝酒吃大席,热热闹闹的。
月兰三叔刚拉回来就来了,该帮忙还是要帮忙的,毕竟是近邻,她提了一包挂面,三叔拉着月兰的手哭了,哽咽着说:多亏你呀!月兰,远亲不如近邻,不是你,那一晚我早就死在门口了,天明了冻得硬邦邦的。三婶打断了三叔的话:看你说的,我还没死吆,你昨说这晦气话?三婶回来就愁眉不展了,这花了十几万元钱,儿子还没有找下对象,还没成家,雪上加霜,看病花了的钱合疗不知能报多少?要是到外面挣,猴年马月才能挣回来呀?这日子昨过呀?来人散了,她只能悄悄伤心地哭泣,自己安慰自己。
过了几天,儿子从广州回来了,但没挣下钱,卡里只有贰千余元钱,这孩子从二十多岁初中毕业了就出门闯荡江湖,在广州谋生,烫着红头发,穿着明晃晃的新衣服和皮鞋,叼着香烟,时尚前卫,与这个穷家格格不入。三叔三婶也不知道在那边整天干啥?问多问少都不说,气得三婶也没办法,由他去吧。如今快三十岁了,也没娶下媳妇,谈是谈了不少,但媳妇就是没有定下来,挣下的钱也不知道花哪里去了?今年谈一个,明年谈一个,有钱了就和女孩子一块浪荡东跑西串,住宾馆去洗浴中心,胡吃海喝,挣的没有花的多。家里饭菜不可口,天天晚上去街道吃夜市。几天工夫,卡里就剩壹千多元了。三婶想张嘴要儿子卡里的壹仟多元,但始终没有张开囗,看着儿子混的那个熊样子,也没忍心要,儿子照看了几天,便厌烦暴躁起来,和三叔顶嘴闹别扭,甚至讽刺挖苦骂三叔,脾气大了还要揍三叔。三叔哭着给月兰都说好几回了,月兰是一个外人,又能怎么样呢?儿子有一天不辞而别了,家要败出妖怪,儿大不由爹,老猫不逼鼠了。谁知道又跑那里去了?现在好多年轻人天南海北打工挣钱看花花世面,大多都是自挣自花,图个快活,不顾家,能攒下大钱的少得可怜,挣下钱不交父母,父母也能忍,只要不给家里伸手要钱就烧高香了。洋不洋土不土,不知道自己哪儿生的,不知道父母过日子艰难。三叔的儿子就是这号人呀。
中间趁这个当儿,家里好歹有儿子照看他爹,三婶也到西安给饭店老板拿了一点特产核桃豆腐干红薯粉条,好说歹说,磨破了嘴皮子说了家里的困难,老板才把她那一点工资结了,结了贰万余元,回来就存信用社了,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用的。当时放存折和身份证时,儿子也看见了,放在柜子底,三婶也没多想。一般来说,饭店老板为了能留住人,年底才结账,农村来的最短都得干半年多,才给考虑工钱,三婶在饭店干了好几年了,人也勤快肯吃苦,干的是倒垃圾洗盘子洗碗洗菜的苦力活,手都泡胀了,睌上要抹凡士林润手,再高档的饭店都离不了这号人,老板可能起了善心,不但放了人,还全额结清。三婶从此专心呆在家了,不想远跑了,一边照看三叔,一边就近打一点零工挣点钱,慢慢熬着日子。
每天早晨或黄昏,三婶要搀扶着三叔到村后路上转一转,名曰活动筋骨加强锻炼。天长日久,春去秋来,坚持了段时间,三婶没那个耐心了。便叫三叔自己随便走去,随便晃荡,想到哪到哪,想走多久走多久,她还要打零工挣钱补贴家用哩。三叔想买一个轮椅,结结巴巴给三婶说了,三婶道:去去去,钱都给你看病了,还买轮椅呢?给你买个火箭坐上。不了了之。村上一户人家修院墙缺小工,三婶给包工头说了,管吃管喝一天壹佰贰拾元。三婶给三叔说:馍馍有哩,方便面给你买下了,你随便吃。这些天我挣钱呀。三叔气得哼哼,咬牙切齿的,也没办法,总不能整天叫婆娘围着自已转,谁叫自己是废人呢?
从此三叔唯一的念想就是准时吃药,多活动,让病好了,多活几年,看到给儿子娶媳妇的哪一天,喝的药空盒盒都积攒一堆了。早上三婶干活去了,他有时泡一点干馍或泡一包方便面将就吃吃,又喝了药,就一瘸一拐地去村后小路上锻炼了,乏了靠住树歇一歇,或坐在路边打打盹小睡一会儿,走得吃力了就走少些,不吃力就多走些。可锻炼了一段时间,身体状况确越来越差了,双腿像灌了铅般沉重,迈步越来越艰难了。月兰见三叔走路困难,有一天给了他一个拐杖,是她和男人以前上华山游玩时买下的,油染的红红的,实木的。她给三叔时说:拐杖是一条腿,撑着慢慢走,千万不要摔了。三叔说:欠你的恩情到阴间还你。唉,久病床前无孝子,谁管我死活呢?自磨自死,还不如死了一了百了,睡到地底下凉凉的,怪美。说着说着就说不下去了,身子抽搐,鼻酸喉噎,不由自主放声大哭了。月兰道:我能看见了就帮帮你,你甭哭,哭得人心里怪难受的,你咋跟娃娃一样?但也不由自主背过身去,眼泪流了下来。
人常说:风来树先摇,病来如山倒。村后的小路上三叔柱着拐杖锻炼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偶尔来一次,他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走累了柱着拐杖靠着树缓缓劲,呆呆傻傻地,看看蓝天白云看看田野庄稼,甚至看看荒草树木及远方的山水房舍,多么熟悉,多么不舍呀!他忽然想起了自已的父亲三十多年前患了食道癌,家里穷得叮当响没钱看病,躺在炕上滴水不进十几天,身架缩小了,矮短了,瘦得皮包骨头,是活活饿死的。他想起了老母亲也是在十几年前一个大清早得了紧病一跤摔倒,吐了一堆,死了,像睡了一觉,没有征兆,没有痛苦,无声无息地驾鹤西去。想着想着,一个人便哭泣,仰天长叹,心情懊丧悲伤到了极点。他还到村后南坡跟的坟场子看了几次,那里是全村人死了埋的地方,树木杂草纠缠在一起,老坟墓土堆堆低落簇拥,野草掩埋,近年新坟墓碑大理石拱门高大泛着青光,墓背野草疯长,旧坟挨新坟,围着坡脚诺大一片,松树柏树黑压压覆盖着亡魂,有的坟头还遗留着褪了颜色腐朽的花圈纸扎,大白天都阴森森地渗人,人都绕着走,想想自己死了埋在那里呀?不由悲伤,眼泪长流。尤其在夜里经常做噩梦,眼皮闭合就与好多死人搅在一块,不是和父母打打闹闹,就是和爷婆大囗吃饭,有时吃的狼呑虎咽,有时吃得香喷喷满嘴流油,在一块来来往往吃住行,恍若隔世。
要知道爷婆都死了快五十多年了,还能梦见,真是活见鬼了。还有与村上的亡人打架斗殴,打的头破血流,你死我活,这些亡人有的是被车撞死的,有的是跳井跳水库跳河的,有的是被砖瓦窑塌死的,有的是在外边务工出了意外,或从高架子上摔死的,或下煤窑下矿洞被煤块子矿石砸死的,死了拉回来的,有拉骨灰盒放棺材里埋了的,有拉尸首缺胳膊少腿头砸得稀巴烂裹了纱布缠了假头放棺材里埋了的。但绝大多数都是自然死的,有年轻的年老的,男的女的,他都熟络,有时哈哈大笑,有时杀人放血,红艳艳的血,另人毛骨悚然。有时是从高处房上树上掉下来,受了惊吓,忽然就醒了,醒来坐起躺下,躺下坐起,反复几次,哀声叹气,泪水长涕,眼睛瞪着天花板,睡意全无,瞪眼到天亮。他不知道是自己多愁善感?还是哪些死人勾自己的魂?小时候听婆爷说红布桃木条子能趋鬼避邪,他在炕头放了,毬事不顶。只要一闭眼一打呼噜就做噩梦,梦见了死人复活,梦见死人在眼前走动大喊大叫,醒来往往是一身冷汗。他也是越来越糊涂了,老年机明明装在口袋里,临出门还乱找,门锁了走出屋门又踅回去了,看到底锁了没有?钥匙拿在手里还低头回头转圈圈找钥匙。私藏了几百元买药钱,找了多久都没找见,坑席底下,鞋洞洞,枕头底下,抽屉柜子里,衣衫包包等等都找遍了,也不知道藏哪儿了?屋里也没旁人,可能是儿子回来那些天悄悄拿走了吧?最倒霉的是大便忘擦屁股,几次拄拐杖都起不了身,跌坐在茅坑边,跌坐在粪便上,费了好大劲才爬起来,勉强提起裤子,提不起了,生殖器尻蛋子露在外面都不知道,那还顾及羞丑。有几次大小便行动迟缓,竟屙在了裤子里了,索性把那裤子一卷扔了,换条裤子。这都是病把人搬到了,都是病害的,谁想得病呢?
这样到了这年冬天里,三叔彻底窝在土炕上了,像一块老榆木疙瘩,白天睡黑天睡,仿佛睡觉是他唯一要做的事情,也就是说没力气再跑了。病情末减轻反而加重了,锻炼不了了,想锻炼也不能再锻炼了。三叔这时更像一头走到暮年的老牛,只能沉重地喘息,静卧不起,任日子如风,一天天刮过,天黑了天明了与自己亳不相干,纯粹是苦熬着日子,这要熬到何年何月呀!
天冷了,上冻了,村里村外也没啥活路了,三婶也没工可打了,干家务活串门子成了常态。一天做二顿饭,做好了给三叔舀些放到炕沿上,三叔想吃了就吃两口,不想吃了就在哪儿放着,有几次不小心撞翻了,倒在了被子上,三叔用手掬起来,颤抖着吃进嘴里,被褥弄得脏兮兮的。三婶给三叔炕下放了一个从工地上拿回家装涂料用过的塑料桶,大小便就在桶里解决,大便能拉到桶里就拉到桶里,瓷慢了就拉在了炕上炕下,为这事三婶有时边清理边嘟囔,骂骂咧咧,说些难听的话,三叔听见了装聋子,权当没听见。有时忙了,几天都不清理,臭哄哄的,骚气难闻,家里来了人都躲得远远的。晚上三婶睡在了另一间房子,有时三叔半夜大哭大闹,喊三婶,或要喝水,或要大小便,或者哪儿不舒服,时间一长,三婶也不应声了,睡自个的,习以为常了。
夜己经很深了,寒风刺骨, 天贼冷贼冷的,一年真快,如白驹过隙,转眼到了年底了,快过新年了。这天晚上下雪了,大雪纷纷扬扬,万物寂静无声,草房子村被大雪覆盖了。这晚从不喝酒的三叔开了一瓶白酒,一嘟噜喝了半瓶子,他想醉死,失去知觉,可睡了一觉,竟出奇的清醒,一时半会没有瞌睡,眼瞪得跟铜铃大,想东想西,想南想北,想自己穷命福浅,生了怪病,时日不多,恨自己的病花了十几万,没捥根,还花了老婆的血汗钱。他无数次想起了阴间的婆爷爹妈,想起了死,想起了远在外边乱跑混饭吃的儿子,儿子今辈子可能也指望不上了,也看不到儿媳妇抱不上孙子了。想起了住在一个屋子,睡在另一房间的三婶,想着想着干哭了几声,眼泪长流。到了后半夜眯眯瞪瞪了,慌慌糊糊的,他亲眼看见那些死人都冲他来了,青面獠牙,满头散发,把他围得水泄不通,围得严严实实,使他窒息而恐惧。那死人和他说话,甚至站在床前骂他打他大笑或大哭,这不知是幻觉还是真的?或者是自己老糊涂了?但稍微清醒,什么都沒有,有的只是死般的寂静,屋里啥都是原样,只是出了一身虚汗。黎明时分,三叔痛苦而又绝望地想到了死,也许死是唯一的解脱和归宿,死了不受苦不遭罪了,到阴间享福了,能见婆爷爹妈了,团圆了,他不想再拖累任何人了,谁也靠不住了,不想再活了,活够了,他要离开这个世界,说白了真是挺不过这一关了。他依靠拐杖的支撑费了很大劲,艰难地挪下了炕,被子褥子卷了一疙瘩,发出了一阵阵酸臭味。他想柱着拐杖立起身来,但身子软了,如雨打的泥巴,又摔了一跤,彻底立不起身了。这次他没有哭,没有喊,他知道哭喊已经没有用了。他使出浑身的劲儿,爬到门口用拐杖拨开门闩,又爬到院子里。像一头受伤的野兽,实在熬不下去了,熬到了尽头,佝偻的身体把积雪爬出了一道痕迹,但不久就被落雪掩埋了。他爬呀,爬呀,终于爬到院子边那一棵光秃秃的核桃树下,他用一生的力气把裤腰带套上了自己的脖子,上吊了。三叔的世界瞬间坍塌消失了,三叔和这个世界再也没有任何瓜葛了。人绝望时会走极端,这不知是不是神鬼的驱使?还是自己稀里糊涂?反正三叔完成了这个动作,人有时硬如钢,有时脆如草,人活一口气,那一口气卡住了,人就没了。人世间再无三叔。
天大亮时,满世界白皑皑的,三叔也白皑皑的,被大雪染白了,与冰天雪地融成了一体。核桃树没有嘶鸣,只是摇晃了一下,便不再摇晃。大雪还在不停地下着,下着,无穷无尽,没完没了。冬天的草房子村村民本来就起床迟缓,一场大雪,村民起床更迟缓了,草房子村寂静了,大雪封村封路封山,零星的狗吠和鸡鸣,落雪的声音“沙沙,沙沙”,发出细微地声响,都埋没在大雪中。
九点多,月兰起来上厕所,倒尿桶,是她先发现三叔的,吓得连滚带爬叫醒了还在被窝里的三婶,村上人闻信赶来了,人们七手八脚把三叔从核桃树上解下来,拍掉了身上的积雪,有人试了试鼻息,没一丝丝气了,全身僵硬,抬到前屋中堂,由村上老者给洗了手脸,换上了寿衣,后生们生了几大盆子木炭煤火,搭起了灵堂。那根红红的柺杖不知咋搞的,竟然断成了二截,月兰发现了,用胶带胶了,放在三叔身旁。当紧的是棺材还没着落,最便宜的一副松木寿材也要伍仟多元呢,柏木的更贵,八九仟元近万呢,家贫,就买一副松木的吧。三婶从柜底子取出存折身份证到街上信用社取钱时,可柜台业务员告诉她:存折上的钱早被人取了。三婶“啊”了一声,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想来想去,存折身份证都在一块好好的,外人不知道呀,只有儿子哪天看见了,可能是儿子拿走了。她手颤的慌,掏出手机拨了几次儿子的号码才打通了,儿子回答的倒爽快,说:是我取走了,我要在这边发展呢。三婶头“嗡”地一声大了:败家子,你爸死了…话没说完便跌倒了,昏死了过去。当初真不该打电话叫儿子回来,贰万多元呢,不知道折腾完了没有?三婶后悔死了。再打,儿子不接电电话了,三婶的心瞬间凉到了脚跟,比冰雪还凉。
是月兰把三婶接回去的,队长牵头,村组垫付了钱,给三叔拉回了棺材,还买回来了米面油菜。安排匠人帮工去坟场子提前挖坑。入殓时,三婶把三叔的旧衣服,老年机,拐杖,喝剩的药,用过的碗筷茶杯统统都塞棺材里了,贴着三叔僵硬变形的尸体。她不想看见这些东西了,看见了就心酸,就反胃,就连三叔铺盖的脏兮兮的被褥,也一把火化为灰烬了。请阴阳先生看过时辰了,三天后午时是三叔出殡的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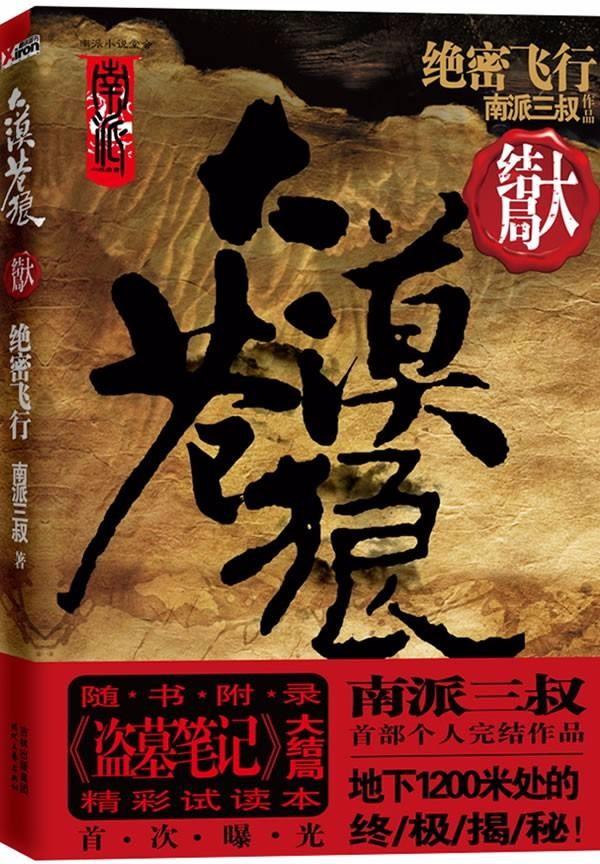
三天后早晨十点多,招待来客吃了饭,午时许,天阴冷阴冷的,雪还没消融,积雪易滑,返着刺眼的寒光。由于天气的原因,草房子村外出的挣钱的人大部分阻隔在外地,村里仅有的二十多个男女老少用大铁架子车装着三叔格外沉重的灵柩,绳拉手推吆喝前行。临行前只在门前烧了一堆黄纸,响了一串鞭炮,没有唢呐,没有乐队,稀稀拉拉,七零八落,向村后五里地的南坡跟坟场子走去。好多人都被落雪滑倒了,但有爬了起来,哈哈气,拍拍雪,继续前行,送葬队伍行动迟缓,显得艰难而漫长。
埋了三叔,三婶劳累地睡倒了,这要打起精神,不知道要到啥时候?
大雪停两天了,天阴沉沉的,见不到太阳,天没有睛的迹象,地上的积雪被人踩得光溜溜的。寒风一吹,偶尔有飘落起了零星的雪花,这个冬天,飘落在三婶心灵上的雪花,何时才能融化呢?
2022年12月22日草改
2023年7月又改
作者简介:
姜福军,八十年代开始写诗,有作品发表,后经商。但对文学一生钟爱,从未放弃!陕西省洛南县人。《作家摇篮》签约作家。商洛诗歌学会会员。有作品发表于《商洛日报》《泸州报》《星期天》《陕西市政》《西北建设》《丹水》《商洛文化》《天竺山》等报刊。
顾问:杨经纬刘剑锋杨克江 萧军
总编:乐俊峰
主编:闫秀民
副主编:李斌
编 委 成 员:
乐俊峰 闫秀民 陈大维 张军锋 杰 布
李卫群 焦 静 徐 娟 李 斌 麻新平
贺自力 闫勇军 若 兰 查 珂 樊会民
王菊玲 蒹 葭 林 溪 赵 鸣 张正阳
杨学艺 蔺爱舍 张建华 门见山 张宁芳
宋瑞林 吴淑娟 冯新勇 吴荣莉 杨峰峰
王宏卫 何玲侠 王爱芳 屈雪芳 李少明
协作单位:彩虹律所
审稿:
宋瑞林(散文)诗歌(五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