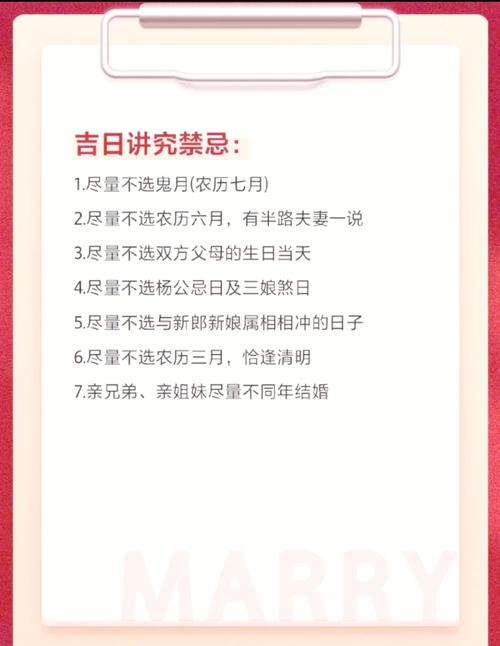命硬的钓鱼人
到飞龙湖垂钓,我喜欢去平桃村余粮沟,到余粮沟垂钓,我喜欢钓一个世界和另个世界连珠合璧的赐予,湖天一色,山长水远,或收之水下,或敛之水外,或徜徉于游目遐想,或快然于谰言清谈,日日上新,一点一滴皆难忘怀。
余粮沟最大的特点就是宁静,少有人去。夏天垂钓,我连续好几日去到那里,每次总在近中午的时候走来一个老头,挺怪,在这个少有人去的地方,我们却能常见。我们相隔甚远,对僻静的选择竟然不约而同。我不愿去别的地方,即使有朋友邀约,也三推四推。他钟爱的缘由我不知道,但我钟爱的缘由我得说,不是那儿一坡上一坡下,山高路陡,直叫人大汗淋漓;也不是多鱼获满载而归,相反我无数次当“空军”无功而返,心里却喜滋滋;也不是山清水秀,风景煞人不忍他去:不是,尽皆不是。这里昼的安谧,夜的清凉,为我们呈献了一个远离纷繁世界的寂寞世界,一个可以把城市的喧嚣弄伤的创痕抚平的理想所在。入眼,不舍;入心,最爱。
去余粮沟的路难,从停车处空手行,单程半小时,负竿包、水饮等近一小时。然而真难的更在于过岭穿林,有时山鸡自路旁草丛扑棱飞出,吓你一跳;有时毒蛇、巨蟒抢道而过,简直不敢信过者的胆气令自然之凶神也生戒惧;有时也有其它精灵踩碎松针、枯叶,发出窸窣的声响入耳,你不得不竖耳提神,谨慎前行。……就这样,或人让于物,或物让于人,每每吓一跳,小心别过。
到晚间,渔灯亮起,或蓝或紫或黄或白,偌大的水湾一两盏渔灯丝毫亮不开夜的宁谧,水中浮游的鱼儿不知有多少,当凄厉的夜鸦声传来,借着渔灯光辉的余角,我看见巨大的黑影扑向水面,接着“唰”的一片响,全是鱼儿入水的声音,像一潭薄冰突然受击碎裂,像地震一瞬间崩塌下大片楼宇。夜再深,星星眨着瞌睡人的眼,渔翁困倦了,夜鸦依然砸击水面,天光倒映,水中隐隐约约露出如头头脸脸的土堆来。其实白天它们也在,唯独到了晚上,当寂静与漆黑包围了世界,四面的暗影狰狞逼来,它们就像可以移动了,令人不禁要想它的下面会有什么,冒出来什么,走来什么,结果什么也没有。夜不吓人,吓人者,自己也。
“吓人!”老头说,“自己更不可能!”
我无意与他攒比,他的胆子我佩服,他姓苟,有名无号,当面我叫他苟老人,背了我称他苟老头。老头今年已80岁,肥硕的身躯,光秃的脑门,肩上的力一百七八十斤,胳膊腿壮得像年轻人。世有奇人,他的奇,恐就是这80岁还很壮实了。
我穿过他一身衣裤。那是2018年夏天,我与文、廖二老师同到余粮沟垂钓,文与苟相识,经文介绍,我们也相识。识归识,毕竟陌生,也不随意说话。钓一阵鱼,倒是苟先开了口。他对文说:“你抽的烟要高级点,没见嘴巴动就冒烟了,我也抽一支,土么土点,你那鬼子货换不了我的土八路噢!”文接过话:“我那渣渣烟,哪配递你老人家哟,真给你你不接,那才方人(尴尬)呢!”他们就这样一句掷过去,一句回过来。乡人们呼之为说砣话。意思是放牛娃游戏扔泥砣子,你一砣子敬过,我一砣子奉陪,嬉闹而已。我与廖不搭腔,只顾听。有时老头故意把话向我们一边引,说:“鱼向你们那边来啰,盯着点!”有时又像小孩在一群人中燃爆一枚惊雷,“早上七八点,下午二三点,鱼要开口拦不住,注意呀!”憋闷的空气顿时流动起来,大家都精神了。那天真奇,下午没有任何先兆,突然一场暴雨袭来,专用钓鱼伞也不能对付,个个都湿透了,于是乎——撤离。
返程翻山,文、廖、老头都快,我掉队了。老头上到山顶又折回接我。多老的人了,暴雨倾盆的时候不是自顾自,而是想到了一个刚刚认识的人,而这个人比他年轻。为此我怎么也不能忘记他!
到了车的地方,老头非要邀请大家,甚至一次又一次吩咐家中老太剖鱼备饭。但文坚持不从,驾车离去,而我与廖去了他家,他老太已把饭菜准备停当,只是我们不得不顾着天晚,就各自换了他一身衣服回家。
因为一身干衣,我和廖没有因雨而生病,而文一身湿衣回去,咳嗽了,为此,我与廖都打心里感激老头!
那件事后,又一天,廖与我同在余粮沟,我们几乎同时发现主河道的山壁上贴着一个人影移动。山壁陡,那人贴不住,不得不一手拄着白晃晃的长竹竿,一手使着短锄头,掏啊刨啊掘啊,调整各种姿势贴行,一段五十余米的距离,足足用了二十余分钟。只一眼,大背篼、短锄头的行头,我们就断定是他。背篼里还有一把小柴刀、一袋包谷碎粒喂料——十来斤、一瓶老玉米钓饵——自制、一块软垫、一壶茶水。那天他不走运,他从一个梨树湾的地方连转三个水湾来到余粮沟,早在经过梨树湾到沙湾的陡坡时他就落水了,仅靠着两根竹鱼竿,他好不容易爬了起来,但是手机淹坏了。为这事他很后悔,自言自语为什么要冒险,凡事都有个万一,要是这事也发生万一,——人们找不到他,他的老伴只能像秋风中的衰草一样迅速地枯黄、憔悴、衰老,熬不过今冬明春就灯尽油干。现在好了,幸运也有一万,夏天过去,秋天又来,今天还和昨天一样,昨天和前天一样,他依然健在,依然那副行头,依然是余粮沟的怪老头!
库区泄水防汛,水位下降。有一天,我的钓位前现出一道直溜的坎,老头说:“快到我家猪圈牛栏的地方了。”我突然一惊,全明白了:老头喜欢到余粮沟钓鱼的秘密就在这儿,行头之重的因由也在这儿。
余粮沟是他祖上的私地,土地下户是他的承包地,两代人都在这里养猪喂牛的生活过。构皮滩建电站征用,他得了补偿,但转手就用了,给女儿治病。借衣物那天我和廖都见过他的女儿,她站在白发母亲的身边,两手秀气地交叉在身前,仍是病恹恹的样子。

他说原本有过一个男娃,可是半大人时就不跟他长了,剩下两个女儿,一个病在眼前,一个嫁得很远很远。“这就是命。”他说,“我的命就是守候三个至亲的人的命。”
有人说老头命硬,上苍在给他加寿,给他强劲的腰板、健康的体质、矍铄的精神,让他承受重压、抗争命运。至亲不老,他就不能老,他不老,余粮沟必得去。希腊神话中有个人物叫安泰,无数次被赫拉克里斯击倒,大地母神盖亚就无数次给他力量,让他强大如初。照此,莫非余粮沟也有老头的母神不成?
今年,国家脱贫攻坚进入决胜之年,镇里的扶贫工作组多次做他的移居工作。他把事情对我讲,我随口说:“好事。”
夏日气温渐高,我歇下一段不往构皮滩去了,等到再有机会见面,他又特邀我去他的家。我去了。他原来的房舍已经拆掉,屋基也翻了土,几口人寄居在本家侄儿的三间弃屋里。侄儿对他好,称说只要叔愿意,弃房就是叔永远的家。我问他移居房的事,他说:“在镇上。”
“那还回来?”
“不劳动不习惯,弄吃的也不习惯。”
那一刻,我又想起那个希腊神话,安泰不可以远离盖亚;而今苟老头不可以远离余粮沟,他的老婆子、病中的女儿不可以远离他,他是盖亚又是安泰,回到原来的地方,笑依然,梦依然,一家子快快乐乐。
社会广阔,人各有志,有人羡慕城市,有人向往乡村,有人喜欢喧嚣,有人酷爱宁静,情思不同而已。季来不误农时,闲来垂钓清流。古代高人雅士穷其一生明白一过的生活,苟老头日日得过。
邻里说:“回了好,几十年一堆坐,也舍不得。”
“天常安而不动,地极深而不测。”移居什么呢?这样就更是一篇新时代的中国版希腊神话了。
(作者简介:余启富,男,1966年农历9月12日出生于余庆县构皮滩镇。贵州教育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现为余庆中学语文高级教师,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散文作品语言清新明丽,意境隽永含蓄。)
说明: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