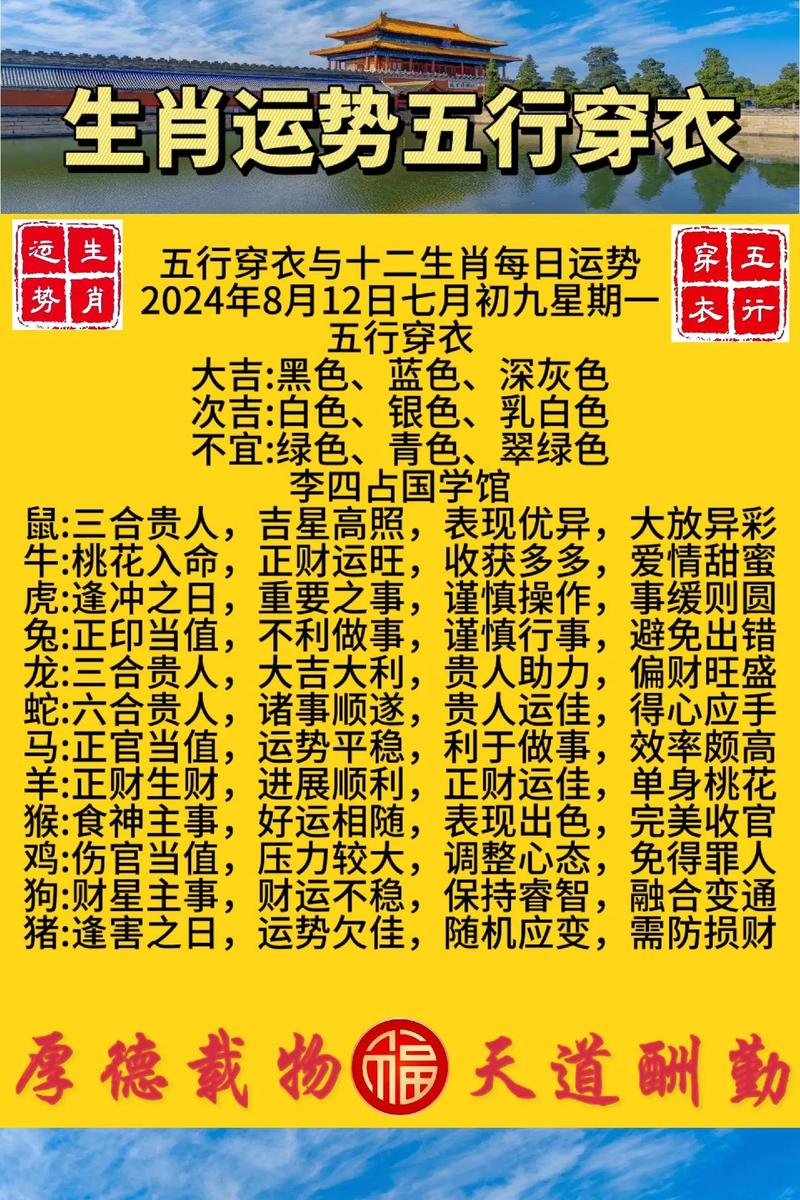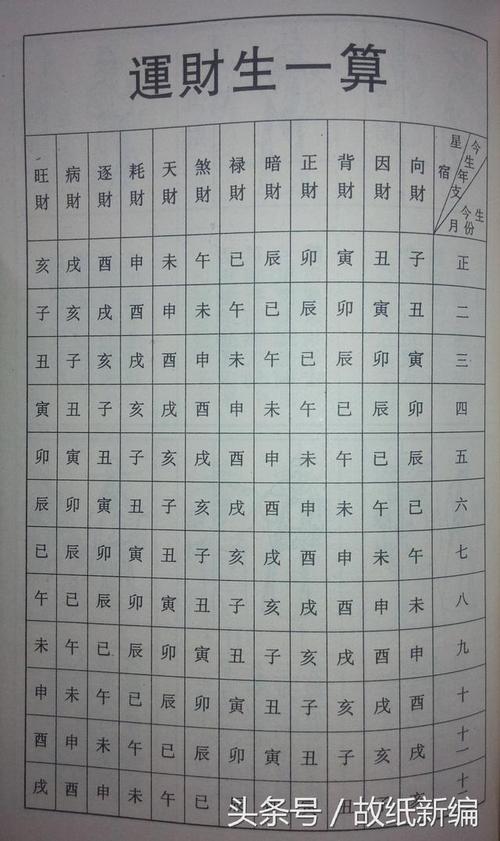70年我用3块饼救下河南乞丐,二十年后他却逆袭成为油泼面馆老板
1.
我这辈子都记着1972年腊月里那个冻死人的早上。供销社后院的煤堆冻得梆硬,我攥着铁锨把儿砸煤,手心里全是汗。新发的蓝布袖套蹭着煤渣子,磨得我手腕子发红——这是爹留下的,他上个月在农机站让皮带轮绞了腿,血糊拉碴的,站长说让我顶工,算工伤补偿。
煤渣子崩进胶鞋里,扎得脚底板生疼。我弯腰倒鞋的工夫,瞅见煤堆后头蜷着团黑影子。凑近了才看清是个人,破棉袄冻得跟铁甲似的,露出的棉花结成冰疙瘩。那人怀里搂着个空布袋子,手指头紫得发黑,指甲缝里糊着泥。
我拿铁锨柄戳了戳他,布袋子角上掉出半块灰石头,滚到雪地里沾了泥。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河南遭灾时吃的观音土。供销社里老马主任正在点红糖,我不敢吱声,糖罐子底下压着三个糖酥饼,油纸包上印着“备战备荒”的红字,本来是给弟相亲用的。
外头棉帘子哗啦一响,碎嘴王婶提着暖壶来打酱油。我慌得把饼往裤腰里塞,冰得后脊梁打颤。黑陶勺碰着玻璃瓶叮当响,王婶抽着鼻子说:“春芳,你这柜台底下咋有甜味儿?”我抄起笤帚假装扫地,饼渣子顺着裤腿掉进“残次品”筐里。
晌午换班,我揣着剩下的饼往砖窑场跑。西北风卷着煤灰迷眼,背砖的排成蚂蚁队。有个佝偻着背的特别扎眼,裤腿用草绳捆着,走一步拖三寸,活像老牛拉破车。我认出他怀里的空布袋子,火车票角让汗浸得发软——郑州到潼关,一块二。
窑场窝棚里炸出会计的骂声:“哪个龟孙动老子的面缸?”我缩在土坡后头,看见那人被揪着领子拖出来,鼻血滴滴答答砸在冻土上。他抓起把草灰捂鼻子,哑着嗓子喊:“霉面掺榆树皮蒸窝头,吃不死人!”围着看热闹的工友哗啦散开,会计的巴掌举到半空,到底没敢落下来。
半夜我蹲在供销社后门烤火盆,棉帘子忽然掀开条缝。那个佝偻影子挤进来,手里攥着把干草叶。我认出是砖窑场那人,他哆嗦着掏出块烤焦的窝头,黑乎乎的像牛粪:“大妹子,俺不白吃你的饼。”
我把火盆往他跟前推,窝头渣子掉进炭灰里滋啦响。他棉袄袖口露出道血口子,草绳捆着块破布。我摸出柜台上给爹留的紫药水,他慌得往后缩:“使不得,俺身上有虱子。”
外头北风嚎得跟狼似的,老马主任的咳嗽声从里屋传出来。我抓起紫药水往他袖口倒,药水顺着破布渗进去,他疼得直抽气,嘴里却念叨:“比俺老家盐碱地腌伤口强。”
后来我才知道,他叫张满囤,家里人都饿死了,揣着半块观音土扒火车来的陕西。那晚他塞给我个草编的蚂蚱,说是拿窑场麦秸掐的。蚂蚱腿断了一根,跟我弟小时候玩的一模一样。
腊月二十三祭灶,供销社分了两斤古巴糖。我偷着留了半把,裹在旧报纸里往砖窑场送。老远就看见满囤在背砖,草绳把裤腿勒出两道血印子。他瞧见我,慌得把砖摞歪了,挨了会计一鞭子。
我把糖塞给他,他手在裤子上蹭了又蹭才敢接。报纸让汗浸湿了,糖粒粘成块。他掰了指甲盖大的一点含嘴里,剩下的揣进贴身布袋:“等开春俺攒够工分,给大妹子捎粉条子。”
那天傍晚飘起雪糁子,王婶来买盐,瞅见柜台底下掉的糖渣子。她嘴撇得老长:“春芳啊,供销社的糖可经不起这么糟蹋。”我抓起鸡毛掸子扫柜台,糖渣子混着灰飞到她鞋面上,她跺着脚骂咧咧走了。
夜里我梦见爹的腿,血淋淋的裤管空荡荡晃悠。惊醒时听见后门有动静,满囤蹲在门槛上,怀里抱着捆干柴。他不敢进屋,把柴火码在墙根,袖口又渗出血,草绳换成新鲜的麦秆。
开春化冻时,满囤的工分攒够了,真给我送来两扎粉条。粉条用杂志内页裹着,他说这样路上不怕查。我煮了一锅酸汤面,粉条吸饱了汤,胀得筷子粗。满囤蹲在门槛上吃,呼噜声震得梁上灰往下掉。
王婶闻着味儿过来,眼珠子黏在碗里:“呦,河南粉条?”满囤慌得端碗要倒,我抢过来搁柜台上:“残次品处理的,婶子要就拿走。”王婶撇撇嘴,扭着腰走了。满囤盯着碗底剩的汤,小声说:“俺老家粉条比这筋道。”
那天我头回见他笑,缺了颗门牙,像个黑瘦的土拨鼠。窗外的老槐树开始抽芽,供销社的石灰墙潮气散了,糖罐里新进了批古巴糖。满囤的草绳换成了布条,走起路还是拖着地,但裤腿不灌风了。
2.
开春化冻那阵子,我男人在农机站出了事。他修拖拉机时让齿轮绞了手,三根指头跟蔫萝卜似的吊在纱布外头。医院药水味呛得人睁不开眼,我攥着缴费单在走廊哆嗦——手术费要八十块,顶我半年工资。
后半夜我蹲在锅炉房门口哭,冷风顺着裤管往上钻。忽然有人往我怀里塞了个热乎的搪瓷缸,抬头瞅见满囤黑黢黢的脸。他袖口沾着油泥,裤腿挽得老高:“春芳姐,趁热喝。”
缸子里炖着黄澄澄的鸡汤,漂着两片姜。我捧着缸子暖手,满囤蹲在台阶上啃冷馍。他脖梗子让晒脱了皮,说是跟着农机队下乡抢修,一天能多挣五毛钱。我问他哪来的鸡,他挠挠头:“河滩地逮的野鹌鹑。”
后来我才知道,他连续半个月翻墙进医院送汤。护士抓着他胳膊要报保卫科,满囤掏出张皱巴巴的介绍信,上面盖着西关大队的红章:“这是俺亲姐!”
那晚我给男人擦身子,发现他秋衣口袋里塞着三块钱。满囤在窗外摆手,月光照见他掌心裂开的口子,像干涸的河床。
麦子抽穗时,满囤往供销社跑得更勤了。有时带把野荠菜,有时是几个野鸭蛋。有回他神秘兮兮地掏出手帕包,里头躺着三个青杏:“河滩地那棵野杏树结的。”
杏子酸得人倒牙,我男人却吃得直咂嘴。他残了的手包着纱布,像半截发霉的馒头。满囤蹲在门槛上啃冷馍,看我男人咂杏核,忽然说:“赶明儿俺种片杏林。”
芒种那天晌午,我正在盘货,外头突然吵吵嚷嚷。满囤背着个姑娘冲进来,那姑娘裤脚沾着泥,辫子散得像草窝。满囤满头汗珠子往下砸:“春芳姐,给口水喝。”
姑娘叫秀娥,是个哑巴。她比划着说自己从三十里外逃婚过来,爹娘要拿她换两头驴。满囤蹲在墙角搓手,草鞋底子磨穿了洞,大脚趾头在外面打晃。
我把秀娥藏在供销社库房,麦麸堆里扒拉出个窝。夜里满囤翻墙进来送馍,秀娥缩在麻袋后头发抖。月光从气窗漏进来,照见满囤胳膊上的血道子——准是翻墙时让铁丝网刮的。
七天后,满囤举着煤油灯跪在村支书家门口。我躲在老槐树后头瞅见,他脊梁骨挺得笔直,灯油滴在棉裤上烧出个洞。鸡叫三遍时,村支书甩出来张纸:“拿先进奖状来换!”
满囤真把抢救窑场的奖状交了上去,换回张结婚证。那天他揣着证来供销社,手指头把衣角搓成了麻花。秀娥躲在他身后,手指头绞着红头绳——那是我给弟媳妇准备的。
秋分那天,满囤在河滩地搭了间窝棚。我去送暖壶时,看见墙上糊满旧报纸,裂缝里塞着麦秸。秀娥蹲在灶台前烧火,火光映得她脸红扑扑的。满囤从梁上取下吊着的布袋,倒出把带壳花生——是他在砖窑场帮工换的。
花生炒得半生不熟,嚼着泛甜。满囤说等来年开春,要在河滩种半亩花生。秀娥比划着往土墙指,我凑近了才看清,墙缝里插着根麦秸编的蚂蚱——跟当初满囤送我的一模一样。
腊月里供销社分年货,我偷着留了半斤白糖。满囤死活不肯要,说秀娥采了野蜂蜜。我去窝棚送糖时,看见窗台上晒着野菊花,秀娥正把蜂蜜往瓦罐里装。
罐子底沉着层黑渣子,准是蜂巢没滤净。满囤舀了勺蜂蜜冲水,甜味儿里带着苦。秀娥比划着让我带罐走,我瞅见她手腕上发紫的掐痕——定是采蜜时让野蜂蛰的。
开春化冻时,满囤的窝棚让稽查队端了。说他私垦河滩地,要没收收成。秀娥抱着装花生的麻袋不撒手,满囤蹲在地头数麦茬,一根根摆得齐整。

我去求老马主任开证明,他叼着烟斗叹气:“河南盲流能落户就不易了。”回来时看见满囤在河滩补种麦子,裤腿扎得死紧,草绳勒进肉里。秀娥跟在后头点种,腰弯得像熟透的麦穗。
夏至那天晌午,满囤顶着日头来供销社。他从怀里掏出包发芽的麦种,说是在河滩试种的冬麦。麦粒让体温焐得发烫,我摸出柜台上给爹留的紫药水——他手上的裂口比去年更深了。
供销社新进了批红双喜暖壶,王婶挑三拣四说掉漆。满囤蹲在门口啃馍,忽然说:“等俺种出麦子,给春芳姐蒸白馍。”外头蝉叫得震天响,石灰墙上的水汽结成珠,吧嗒掉在红糖罐上。
3.
供销社货架上的暖水瓶积了灰,外头集市的摊子五颜六色晃人眼。我蹲在库房点货,蜘蛛网缠着算盘珠子,老马主任退休前留的账本潮得卷了边。后窗飘来菜籽油香,混着热辣辣的炝锅声——满囤承包的公社油坊开张了。
那天晌午头,满囤夹着红绸布包冲进供销社。他胳膊肘蹭着玻璃柜台,鎏金匾额上“满囤油泼面”几个字晃得人眼花。我摸着匾额边角的木刺,忽然想起七年前煤堆后头蜷着的人影,如今他棉袄换成了的确良,袖口还别着英雄牌钢笔。
油坊开张那天,我蹲在门槛上剥蒜。秀娥系着碎花围裙跑堂,油点子溅在围裙上像撒了把芝麻。满囤抡着铁勺浇辣子油,滋啦声里腾起白烟,熏得梁上燕子直扑棱。后墙根摞着印“长城牌”的旧暖壶,被他改成量油的家伙什。
秋分那天暴雨来得邪乎,我在供销社对账,算盘珠子越打越慢。外头炸雷劈断老槐树枝,满囤浑身淌水撞进来:“春芳姐,借搪瓷缸子!”他裤腿裹着泥,怀里油桶渗着黄水。我跟去油坊才看见,暴雨冲塌库房顶,三十斤新榨的菜籽油泡了汤。
满囤蹲在漏雨的库房里,拿搪瓷缸子舀水油。我摸出供销社积压的毛巾,大伙排着队拧油水。油花子漂在水面上,聚成铜钱大的圆斑。秀娥把油缸子架在煤炉上隔水热,油腥味呛得人直咳嗽。满囤袖口让油浸得发亮,指头被热气烫出泡。
那批油到底救回来大半,油坊墙上从此留了片烟熏印子,像幅水墨画。满囤说这是招牌,夜里油灯照上去,影子活像尊弥勒佛。
腊月里集市冒出好几家油坊,塑料桶上贴着红纸,价钱比我们便宜三毛。满囤蹲在油桶前闻味道,指甲盖挑了点油捻开:“掺了棉籽油的,烧锅泛黑烟。”他连夜给自家油桶系红布条,扯着嗓子在集市喊:“掺假油烂手心的!”
开春我儿子高考落了榜,躲在库房撕课本。他偷拿供销社的英雄钢笔,说要送给招生办的。满囤蹬着二八杠追到省城,车把上挂的油壶叮咣响。回来时他掏空裤兜,零钱里夹着张复读缴费单:“娃他舅给的。”
我去油坊还钱,看见梁上吊着半扇腊肉。满囤蹲在石碾旁擦锈,说把买新榨油机的钱挪用了。秀娥比划着让我看墙角,那摞糖酥饼油纸糊成的防潮层,最顶上那张还沾着1972年的糖渍。
夏至那天假油贩子找上门,拎着菜刀要拼命。满囤舀起一勺油当众点火,蓝火苗蹿得老高,油花子噼啪炸成莲花状。人群里有后生喊:“这叫青莲真火!”假油贩子缩着脖子溜了,满囤的棉鞋让油星子烧出窟窿。
我儿子复读住校后,满囤常往供销社送油辣子。玻璃罐子用当年装水果糖的樽子装着,辣子上漂着白芝麻。王婶来买盐,盯着辣子罐咽口水:“河南人做辣子倒凶得很。”我挖了勺辣子递过去:“残次品处理的。”
白露那天,满囤从河滩地扛回麻袋新收的花生。油坊院里支起大锅炒料,花生壳在灶膛里哔啵响。秀娥把炒糊的花生挑出来,穿成串挂屋檐下,说是驱虫。我去送盐罐子,看见满囤在剥花生,指甲缝里嵌满红皮。
他挑出粒特别饱满的塞给我:“留着当种子。”花生仁在掌心滚烫,我忽然想起七年前他塞给我的青杏。供销社的挂钟当当响,外头集市的喇叭开始放《在希望的田野上》。
霜降前夜,我男人旧伤发作疼得打滚。满囤蹬着三轮车来送止痛片,车斗里垫着当年装糖酥饼的油纸。药片让汗浸湿了,他蹲在门槛上搓手:“托农机站老伙计捎的。”
我给男人喂药时摸到他兜里的烟盒,里头塞着张皱巴巴的欠条——满囤买榨油机借了三百块,月息三分。窗外的油坊亮着灯,秀娥在院里筛花生,身影投在墙上像皮影戏。
立冬那天,供销社处理最后一批积压货。满囤买走所有印着“备战备荒”的油纸,说要包油饼用。我蹲在柜台底下翻出个锈铁盒,里头是七年前他编的草蚂蚱,腿早让耗子啃光了。
油坊飘来新油香时,我正给儿子收拾复读资料。满囤在窗外招手,递进来个牛皮纸包。里头是省城买的复习题,扉页上歪歪扭扭写着:“给咱外甥。”
小寒那天,我偷着给油坊送了两捆柴。满囤在熬油渣,烟气顺着墙缝往外钻。秀娥忽然拽我衣角,指着梁上挂的腊肉直比划——那肉皮上用刀刻着“春”字,油汪汪的像镀了金。
年三十守岁,满囤端来海碗油泼面。辣子红得透亮,底下埋着荷包蛋。我男人嘬着面汤说:“比卫生院病号饭强。”外头爆竹炸响时,满囤摸出个红包塞给我儿子,里头是张崭新的大团结。
开春供销社盘点,货架上的暖水瓶终于清空了。满囤把空壳子改成量油壶,壶嘴上绑着红布条。我去油坊送账本,看见他蹲在院里挑麦种,裤腿上沾着油渍和泥,跟七年前在河滩地时一个样。
4.
供销社门前的泡桐树开紫花那年,我蹲在库房数最后一批劳保手套。霉味儿钻进鼻孔,跟二十年前一个样。墙角的铁皮糖罐早生了锈,底下压着张泛黄的账本,红钢笔画的歪扭小人还举着饼状太阳——那是1972年张满囤欠的三个糖酥饼。
满囤的面馆扩建拆墙,露出当年糊在墙里的油纸。秀娥端着浆糊盆子站在废墟里,糖渍在太阳底下泛着琥珀光。她比划着让我看油纸上的裂口,那纹路活像人老了手背上的青筋。
集市上开始卖“康师傅”红烧牛肉面,塑料包装红得扎眼。满囤蹲在面馆门槛上研究调料包,老花镜滑到鼻尖。他指甲缝里嵌着辣椒面,指着配料表上的小字:“河南焦作的葱干子。”
后半夜我起夜,瞧见面馆亮着灯。满囤往绿布包里塞衣裳,秀娥正拆毛衣。织了五年的蓝毛线缠成团,毛线票皱巴巴压在搪瓷缸底下——1987年纺织厂倒闭前发的。她把钱卷成筒,塞进满囤裤腰暗兜,针脚密得蚂蚁都钻不进。
满囤走的那天,我把供销社的老算盘买下来。儿子蹲在门口按计算器,按键叮咚响着游戏机声。算盘扔在腌菜缸边上,梁上刻的粮价数字让盐水泡发了胀。满囤的徒弟来修算盘,拿油坊的熟桐油泡珠杆:“当年师傅在窑场画火道图,用的就是这油。”
面馆歇业的第七天,满囤扛着麻袋从河南回来。他掏出一把脱水香葱让我闻,衣裳兜里掉出张郑州站台票。秀娥煮了锅炝锅面,满囤把调料包抖进去,热气腾起来那刻,他忽然说:“还是咱的油泼辣子香。”
王婶的孙子吃坏肚子,半夜拍面馆的门。满囤开送货车逆行让交警拦在卫生院门口。他掏遍所有口袋,零钱里混着1972年的全国粮票。警察捏着粮票直摇头:“老师傅,这早过时了。”
我给王婶送红糖时,看见她床头摆着满囤送的蜂蜜罐。罐底沉的黑渣子还在,上头飘着层白沫。王婶嘴硬:“河南人就会整这些花活。”可她孙子喝蜂蜜水时,她到底没拦着。
供销社改成下岗缝铺那天,我抱着算盘站在泡桐树下。满囤从面馆捧出个陶罐,里头是二十年的油泼辣子。最底下沉着糖酥饼碎渣,混在辣椒籽里像星星。他舀了勺辣子抹在算盘梁上:“这下带着甜味儿了。”
秀娥忽然拽我袖子,指着自己喉咙“啊啊”叫。满囤从抽屉取出针盒,里头躺着半截甘草——原来这些年他给秀娥抓药,每副都多加这味甜根。晒干的甘草片在舌尖化开,供销社的老挂钟正好敲响下班铃。
满囤把面馆招牌改成“春芳油泼面”那天,我翻出压箱底的蓝布袖套。柜台裂缝里卡着的糖纸还在,算盘珠子上凝着辣子油。儿子在对面开小卖部,冰柜里摆满康师傅。满囤蹲在门槛上挑辣子,白头发里沾着红籽,跟当年煤堆旁那个黑影子重叠又散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