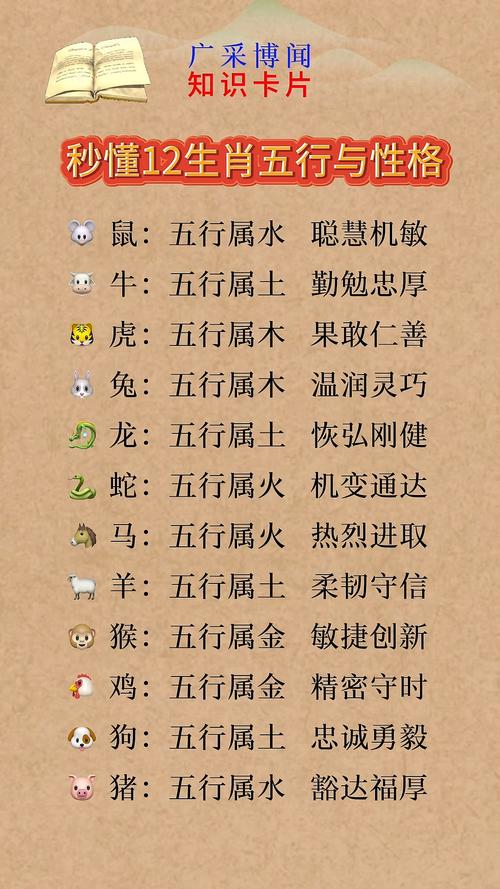春节连做三个梦,老公吓得赶紧去买了半只羊,亲人的感应好神奇
"翠兰,你怎么又坐起来了?"老公迷迷糊糊地问我。
我摸了摸额头的冷汗,望着窗外的月光,心里发慌。夜深人静,只听见老公均匀的呼吸声和外面偶尔传来的狗叫。
"没事,你睡吧。"我轻声回答,却再也睡不着了。
我叫王翠兰,今年四十五岁,是县城纺织厂的女工。八十年代初,我和老公李国强从大队搬到了县城,在单位分的楼房里住下了。
这是一间三十多平米的筒子楼,老式的木门总在冬天缩紧,开关时嘎吱作响。简易的水泥地面上铺着我们结婚时置办的那张暗红色地毯,已经有些磨损了。
国强在县机械厂当钳工,是个手艺人。他那双手,常年带着机油和铁屑的气味,粗糙得像砂纸。但正是这双手,养活了我们一家三口,供儿子上了高中。
儿子国旺今年上高二,正是用功读书的时候。那孩子从小就聪明,却不像我和国强那样安分,总想着离开这个小县城,到大城市闯一闯。
"等考上大学就解放了!"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我和国强听了只是笑,心里却美滋滋的,觉得吃再多苦也值得。
日子虽不富裕,但也算过得去。我们有工作,有住处,还有即将考大学的儿子,这在我们那个年代,已经是很体面的生活了。
只是自从父亲去世后,我便很少回老家。不是不想回,是忙,真的太忙了。
厂里赶订单加班,儿子的学习需要操心,家务活一大堆,哪有时间隔三差五地赶回乡下去?电话还没普及,寄封信都要等半个月才能收到回音。
每次想起父亲,我心里就有一丝愧疚。老人家一辈子没出过那个村子,种了一辈子地,供我上完了初中。
他总说:"闺女,你有出息,爹就知足了。"
父亲是在三年前去世的,那时正值隆冬。我得到消息时,老人已经入土了。乡下的风俗,人一断气就要下葬,哪能等在外地的亲人回来。
当时我哭得昏天黑地,连着好几个月都梦见父亲站在老家的土炕边,用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搓着他心爱的旱烟袋。
春节前三天,我连续做了三个相同的梦,都是父亲站在老家的院子里,瘦骨嶙峋,望着锅台,欲言又止。
梦里的父亲比生前瘦多了,脸颊凹陷,眼窝深深地陷了进去,像是饿了很久很久。我每次想靠近他,他却转身消失在黑暗中。
每次我从梦中惊醒,心跳如雷,总觉得有什么事要发生。这三晚上,我都是惊醒后再也睡不着,坐在床边发呆到天亮。
"国强,我爹又来我梦里了。"清晨,我坐在床边低声说。
"做梦而已,别多想。人都走了三年了,你就是想他,所以梦见他。"国强翻了个身,声音含糊。
"可是,这次不一样。"我紧紧攥着被角,"爹看起来好像很饿的样子。"
国强打了个哈欠,坐起来,摸索着穿上棉袄:"行了行了,明天就过年了,厂里不是发了奖金吗?买点好吃的,好好祭祀一下老人家就是了。"
"嗯。"我点点头,起身去厨房准备早饭。
冰冷的水龙头一拧开,就吐出刺骨的凉水。我搓了搓手,用袖子擦了擦眼角的泪。
厨房里有一张照片,是父亲六十大寿时拍的。老人坐在村口的石磨盘上,穿着我送他的那件深蓝色的确良衬衫,头发已经全白了,但笑得像个孩子。
那是他最后一次过寿,我还记得那天杀了半只羊,请了全村的人来吃饭。父亲爱吃羊肉,说羊肉壮身子。
"爹,你是不是饿了?"我对着照片轻声问。照片中的父亲只是笑,没有回答。
早饭是稀粥配咸菜,国强狼吞虎咽地吃完,拿起挂在墙上的钥匙就要出门。
"今天不是放假吗?"我有些意外。
"车间还有点活,上午去处理一下。"国强说,"你今天别胡思乱想了,去街上买点年货,给国旺买身新衣服。"
"嗯。"我点点头,看着他离开。
收拾完厨房,我坐在窗边发呆。窗外是一排排相似的筒子楼,远处是县城新建的百货大楼,灰蒙蒙的天空下,一切都显得那么单调乏味。
这个冬天特别冷,寒风刮在脸上像刀割。我裹紧了棉袄,拿着菜篮子下楼去。
楼下碰见了邻居张大娘,她是个热心肠的人,丈夫是县委办公室的干部,比我们家条件好多了。
"翠兰,这是要去买年货啊?"张大娘笑眯眯地问。
"是啊,大娘,您也是?"
"可不是嘛,这不,儿子媳妇要回来过年,得多准备点好吃的。"张大娘拍了拍我的手,"翠兰,你这几天看起来脸色不太好啊,是不是又加班了?"
"没,就是这几天睡得不好。"我勉强笑了笑。
"年轻人,别太拼了。"张大娘叹了口气,"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可不能累坏了。"
我点点头,和张大娘一起走向街市。
县城的街市这几天格外热闹,家家户户都在采购年货。肉摊前排着长队,卖鞭炮的小贩声音嘹亮,卖糖果的小推车边围满了孩子。
我站在羊肉摊前,想起父亲。每到过年,他总会和村里人凑钱杀一只羊,然后大家一起分着吃。那时候,肉是多么珍贵啊,一年到头也吃不上几回。
"大姐,要点啥?"卖肉的小伙子问。
我犹豫了一下:"来两斤羊肉。"
"这个月羊肉贵,十块八一斤。"小伙子说。
"这么贵?"我心里一惊,这两斤羊肉就要花掉我小半个月的工资。
"过年嘛,都涨价了。"小伙子无所谓地说。
我咬咬牙,从布兜里掏出钱,数了二十块钱给他。
回到家,国强还没回来。我把羊肉放进冰箱,然后坐在沙发上发呆。
傍晚,国强回来了,手里提着一个纸袋子。
"买了什么?"我问。
国强神秘地笑了笑,从袋子里拿出半只羊的前腿:"你不是说你爹来梦里了吗?我想着,买半只羊,好好祭祀一下。"
我惊讶地看着那块足有十多斤的羊肉,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你这是干啥?"国强被我的反应吓了一跳,"不是你说你爹饿了吗?我寻思着,老人家生前最爱吃羊肉,咱们就买只羊,好好供一供。"
我哭着点点头,扑进国强怀里:"谢谢你。"
国强拍拍我的背:"行了行了,别哭了。快去做饭吧,我肚子都饿得咕咕叫了。"
第二天一早,我起床时,发现国强已经在厨房忙活了。
"你起这么早干啥?"我揉着眼睛问。
"炖羊肉呗,你不是说要祭祀你爹吗?"国强头也不抬地说。
我走过去,看见锅里的羊肉正咕嘟咕嘟地冒着泡,香气四溢。国强把羊肉切成了大块,放了葱姜蒜和八角,还加了些陈年老酒。
"你什么时候学会炖羊肉了?"我惊讶地问。
"以前在农村不就会吗?"国强笑了笑,"你爹在世的时候,我们一起喝过酒,他说他最爱吃羊肉,非说羊肉大补。我还记得你爹那句话:'好女婿,俺这辈子吃过的最好的东西就是羊肉了!'"
我鼻子一酸,又想哭。没想到国强还记得这些事。
正当我们忙活的时候,电话铃响了。国强去接,听了一会儿,脸色突然变了。
"怎么了?"我紧张地问。
"是村里的李大娘,说她病了,问咱们能不能回去看看。"国强放下电话,皱着眉头。
我和李大娘没有血缘关系,但她是我们村的邻居,和我父亲关系很好。自从父亲去世后,是她在照看父亲的坟墓。
"要不,咱们明天回去一趟?"我犹豫地说。
国强点点头:"也好,正好把这羊肉带回去,祭祀一下你爹。"
当晚,我再次梦见了父亲。这次他不再站在锅台边,而是坐在老家的院子里,笑眯眯地看着我,就像他生前那样。
第二天一早,我和国强收拾好行李,带上炖好的羊肉,搭上了回村的班车。

车上人不多,除了我们,还有几个回乡过年的打工仔,他们大包小包的,脸上带着疲惫和期待。
班车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窗外的景色从县城的水泥楼房逐渐变成了田野和村庄。熟悉的景色让我既亲切又陌生,三年没回来了,一切似乎都变了,又似乎什么都没变。
下了车,还要走半个小时的山路才能到村子。国强提着行李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心里忐忑不安。
路上,我一直心神不宁。想起父亲生前的样子,想起他送我出门时的叮嘱,想起他最后一次见到我时,那双浑浊的眼睛里的不舍。
"慢点走。"国强回头对我说,"路滑。"
我点点头,小心翼翼地走着。冬日的阳光洒在山路上,照在我们的身上,却没有多少温度。
远远地,村子的轮廓出现在视线里。土黄色的房子,灰色的烟囱,偶尔有几棵光秃秃的树,一切都是那么熟悉。
父亲的房子在村子的最北边,是一座四合院式的老房子,已经有些年头了。
推开院门,一股冷清的气息扑面而来。院子里冷冷清清,锅台上落了厚厚的灰。院子正中的那棵老槐树还在,但已经枯萎了不少。
"好久没人住了。"国强说,"先去看看李大娘吧。"
李大娘家就在隔壁。我们敲开门,一个年轻女子开了门,是李大娘的孙女小玲。
"翠兰姨,国强叔!"小玲惊喜地叫道,"你们终于来了!奶奶等你们好久了。"
我们跟着小玲进去,看见李大娘躺在炕上,脸色蜡黄,但看见我们,老人家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
"翠兰,国强,你们可算来了。"李大娘艰难地撑起身子,"我这病也不是什么大病,就是想见见你们。"
我赶紧上前扶住她:"大娘,您慢点,别着急。"
坐在炕边,李大娘拉着我的手,眼里泛着泪光:"你爹走了三年了,你一次都没回来看过他。"
我低下头,心里愧疚难当:"大娘,我不是不想回来,是真的太忙了。"
"我知道,我知道。"李大娘拍拍我的手,"你爹临走时也是这么说的,说不要你们常回来奔波,他知道你们在城里不容易。只是每年清明和年节,希望你们能记得他。"
我点点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对了,"李大娘突然想起什么,"昨天我迷迷糊糊睡着,梦见你爹站在我家门口,说你要回来了,让我别担心。今天一早,小玲去县城打电话给你们,没想到你们真的要回来了。"
我呆住了。这就是血脉的感应吗?隔着生死,父亲仍惦记着我,用他的方式提醒着我。
"翠兰姨,你们带的什么?好香啊。"小玲指着我们放在一旁的食盒。
"羊肉。"国强说,"给老人家炖的。过年了,咱们一起吃。"
"羊肉啊!"李大娘眼睛一亮,"你爹最爱吃羊肉了。年轻时他在公社当仓库保管员,有一次过年,公社发了些羊肉,他舍不得吃,全带回家给你们娘俩了。"
这事我倒是第一次听说。我父亲是个寡言的人,很少提起过去的事。
"大娘,我们打算去看看我爹。"我站起身,"您好好休息。"
李大娘点点头,又拉住我的手:"去吧,你爹坟上的柏树都长高了,他会高兴的。"
出了李大娘家,我和国强带着那盒羊肉,向村后的小山坡走去。
父亲的墓在村后的小山坡上,和村里其他老人的墓在一起。墓前立着一块简单的石碑,上面刻着父亲的名字:王德胜。
生前勤劳朴实的一辈子,死后也只剩下这么一块小小的墓碑作为见证。我跪在墓前,心如刀割。
国强帮我把羊肉摆好,又点上了香。
奇怪的是,刚才还阴沉的天,在我们摆好供品的一刻突然放晴,一缕阳光恰好照在墓碑上,周围的云雾也渐渐散去。
我跪下来,眼泪止不住地流:"爹,女儿不孝,这么久没来看您。"
"您放心,我和国强日子过得去,国旺也争气,今年高考,肯定能考上大学。"
"爹,我给您带了羊肉,是您最爱吃的。女儿知道您惦记着我,这不,我梦见您了,就赶紧回来了。"
不知为何,说着说着,我心里竟不再那么难过了。反而有一种释然,一种安宁。
就在这时,一阵风吹过,墓前的香忽然直立起来,烟雾笔直地向上升去,没有一丝偏斜。
国强在一旁惊讶地看着这一幕:"我还从没见过香烟这么直的。"
"这是好兆头。"不知何时,李大娘的孙女小玲来了,站在我们身后,"老人家接受了你们的祭祀。"
我回头看着小玲,她穿着一件旧棉袄,脸被冻得通红,但眼睛里闪烁着明亮的光。
"小玲,你怎么来了?"我问。
"奶奶让我来告诉你们一件事。"小玲说,"我奶奶说,你爹生前有个心愿,想看看你们在县城的家,但他一直不好意思说。"
我心里一震,想起父亲生前最后几年,每次我回来,他都会问起县城的事,问我们住在哪里,房子什么样,但从未提过要去看看。
"你奶奶怎么知道的?"国强问。
"你不记得了吗?"小玲说,"你们结婚那年,爷爷去世没多久,我奶奶和你爹处得来,经常一起唠嗑。你爹总跟我奶奶说,想去县城看看女儿女婿的新家,但怕给你们添麻烦。"
我和国强相视一眼,眼里都是愧疚。
"我们当时太忙了,"国强低声说,"总想着等有空了,接老人家去住几天,可是一直没腾出时间。"
"然后就来不及了。"我哽咽着说。
小玲点点头:"我奶奶说,你爹临终前还惦记着这事,说死后也想看看你们的家。"
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连续三晚梦见父亲。他不是饿了,他是想去我们家看看。
"国强,"我转向丈夫,"咱们明天带点土回去,放在家里,让爹也看看我们的家。"
国强点点头,眼里闪烁着泪光。
祭祀完父亲,我们回到了老家。屋子里尘封的气息让我鼻子发酸。这里盛满了我的童年记忆,每一个角落都有父亲的影子。
那晚,我们住在老家,小玲帮我们打扫了屋子,生起了炉子。炖羊肉的香气弥漫在整个屋子里,就像父亲在世时那样。
夜深人静,我躺在儿时睡过的炕上,听着窗外的风声,突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宁。
梦里,我看见父亲坐在我们县城家的沙发上,笑眯眯地看着电视。他不再瘦骨嶙峋,而是一如生前那样,健壮而满足。
"爹,您还想吃羊肉吗?"我在梦中问。
父亲笑着摇摇头:"不饿了,不饿了。"
第二天清晨,我和国强从父亲的坟前取了一些土,用红布包好,准备带回县城。
临走前,李大娘拉着我的手说:"翠兰,你爹泉下有知,一定很欣慰。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现在看你过得好,他也就安心了。"
回家路上,我望着渐暗的天色,心里却亮堂起来。城市的生活再忙碌,也不该忘记田野上的根;物质再丰富,也替代不了那份血脉相连的牵挂。
回到县城的家,我和国强在客厅的角落里放了一个小木盒,里面装着从父亲坟前带回的土。国强还在盒子旁边放了父亲的照片,照片里,父亲穿着我送他的那件深蓝色的确良衬衫,笑得像个孩子。
那天晚上,我烧了一桌子好菜,其中就有父亲最爱的羊肉。我们一家三口坐在一起,我还特意在父亲照片前放了一双筷子,一个碗。
儿子国旺刚开始有些不解,但当我讲述了这次回乡的经历,他也若有所思。
"妈,我会努力考上大学,让爷爷在天上也为我骄傲。"国旺认真地说。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父亲就坐在我们中间,和我们一起吃着年夜饭,一起笑着,一起憧憬着未来。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梦见父亲站在锅台边欲言又止的样子。偶尔梦见他,都是他坐在我们家的沙发上,笑眯眯地看着我们生活的样子。
有些爱,是无言的守候;有些情,是超越时空的呼唤。这春节的梦境,像是父亲给我的一次生命启示,让我懂得了亲情的分量,也让我明白了,不管我走多远,心中的根永远连着那片生我养我的土地。
后来的日子里,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每逢春节和清明,总会回老家看看,给父亲上坟,炖一锅他最爱的羊肉。
国旺考上了北京的大学,当他穿着学士服的照片摆在父亲的木盒旁时,我仿佛看见父亲欣慰的笑容。
或许,这就是生命的传承,是逝者对生者最深的牵挂,也是生者对逝者最好的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