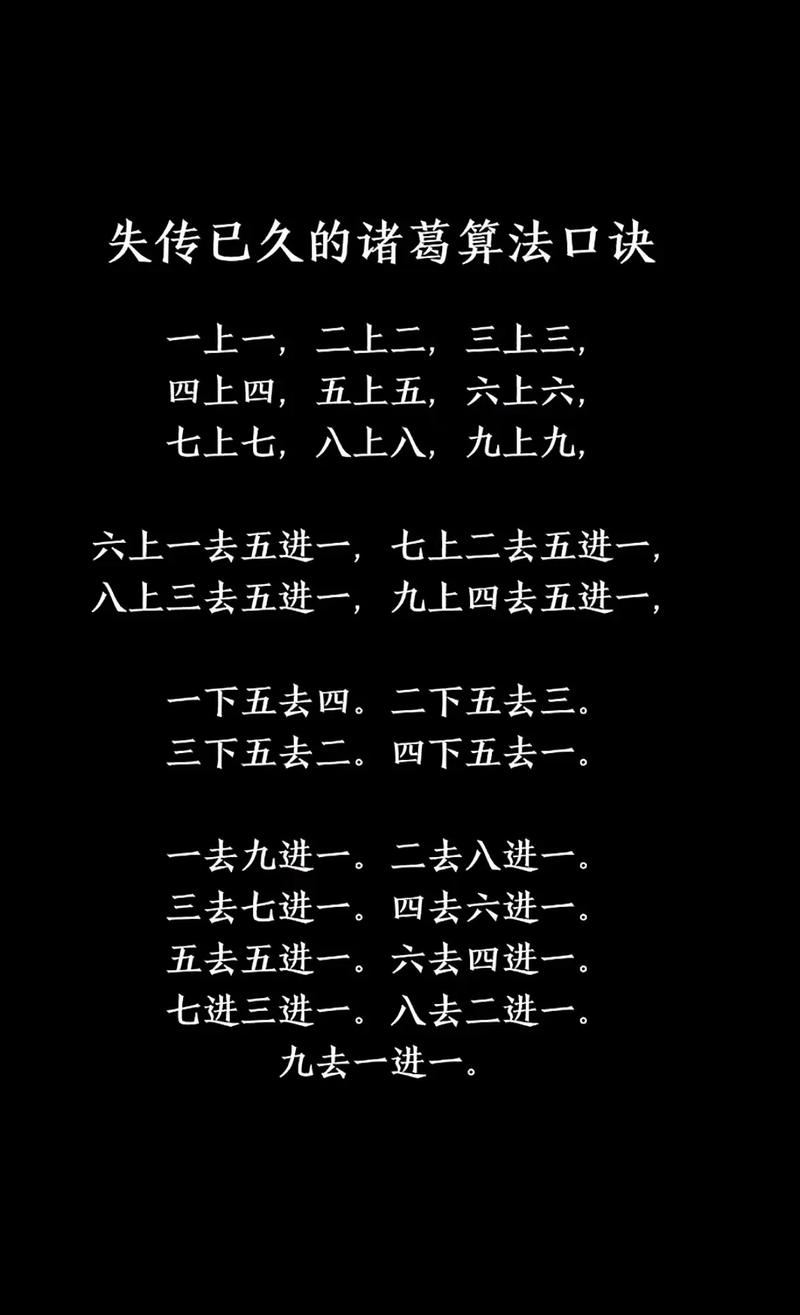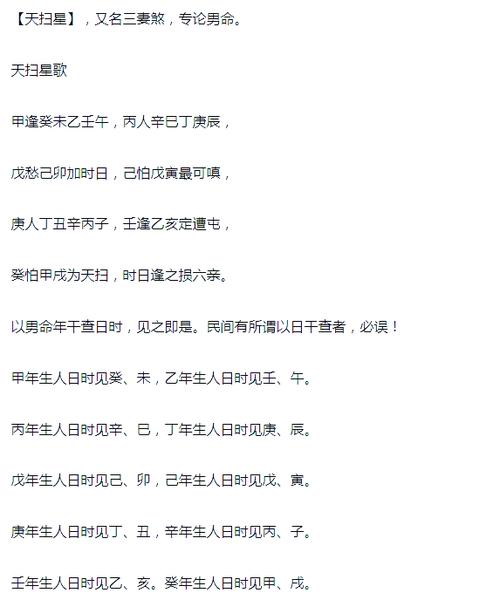春节连做三个梦,老公吓得赶紧去买了半只羊,亲人的感应好神奇
"乡里来信说家里下雪了,可我连着三晚都梦见我娘瘦得皮包骨头,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我放下筷子,忧心忡忡地对丈夫老王说。
那是一九九九年的冬天,窗外北风呼啸,寒气逼人。
老王抬起头,嘴角还沾着饭粒。他搁下筷子,轻轻叹了口气:"又梦见你娘了?"
"嗯,这已经是第三天了。"我拨弄着碗里的白菜,突然没了胃口。
我和老王在县城开了家小百货店,那时候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国营商店日渐式微,个体户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我们的日子过得还算滋润,至少比在乡下刨地强多了。
屋内的煤炉子烧得正旺,发出哧哧的声响。老王起身添了块煤,那是从集市上买来的蜂窝煤,一年四季都少不了的东西。
"梦是假的。"老王嘴上这么说,却放下了半碗没吃完的饭,拿起搪瓷杯喝了口水,眉头紧锁。
那个搪瓷杯是我们结婚时从家里带来的,白底蓝边,杯沿已经磕出了几个小缺口,却舍不得丢。就像我和我的乡愁,破旧却割舍不下。
窗外飘起了雪花,像是天上撒下的盐粒。老王起身去关窗户,手触到窗框时突然顿了顿:"梦连着做三天,真有点邪性。要不,咱回趟老家?"
这话让我愣住了。自从八年前嫁到县城,我回老家的次数一只手就能数过来。
每次回去,娘总会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张望,远远地看见我们就笑得合不拢嘴,一边擦着手上的面粉,一边高声喊:"我闺女回来了!"然后转头冲着邻居家的王婶子喊:"婶子,快来看看,我家闺女回来了!"
娘总会说:"咱家闺女有出息,嫁到城里去了,住楼房,睡席梦思,吃白面馒头。"言语间满是自豪,尽管我和老王最初住的是单位分的半间平房,挤在一张木板床上,连个像样的席梦思都没有。
那时院子里的广播喇叭天天放着《东方红》,我和老王起早贪黑地干活,就是为了能有朝一日过上好日子。
工资袋里的票子一张张攒起来,日子也一天天好起来了。可这几年,随着生意越做越好,我和老王忙得脚不沾地,连春节都没回去过。只是每月固定给家里寄五十块钱,外加过年时的一百块压岁钱。
"这不快过年了吗,到时候一起回去看看。"我试图安慰自己,指了指墙上的挂历,那是烟厂送的宣传品,上面印着穿旗袍的女明星,鲜艳夺目。
老王却异常坚定:"不行,得现在去。我记得你说过,你娘生前最爱吃羊肉,做梦都想着。"
老王这话勾起了我的回忆。娘确实爱吃羊肉,但那是何等奢侈的东西。记得小时候,生产队杀年猪,分到各家各户的肉也就巴掌大的一块。而羊肉,那是过年才能见着的稀罕物。
娘总说,她年轻时怀着我的时候,就特别想吃羊肉。可那时候哪有羊肉吃?爹跑遍了邻村,好不容易从一个养羊的老汉家换了半斤羊肉回来。娘吃了,说那是她这辈子吃过的最香的东西。
"记得娘生前总念叨,死后去了那边,也要吃顿羊肉暖暖身子。"我的眼眶红了,声音哽咽。
老王放下杯子,认真地看着我:"那就买半只羊,带回去,祭祭你娘的坟。顺便看看你弟他们,这么多年没回去,也该去看看了。"
说完,他转头看了一眼店里的货架,那上面摆着一排南方来的保温杯,往年这个时候早卖光了,今年却不知怎的,堆在那里落了灰。
"店里生意最近也不好,关几天也无妨。"老王摸了摸下巴上的胡茬,若有所思。
那晚,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躺在床上,听着墙上的钟表滴答作响,想着八百里外的老家,想着已故的娘亲,想着许久未见的弟弟一家。
院子里的老槐树下,娘总会坐在那里做针线活,一边哼着当地的小调,一边絮絮叨叨地讲着村里的新鲜事。她的手上总是有着厚厚的茧子,那是多年操劳留下的痕迹。
想着想着,泪水湿透了枕巾。
第二天一早,老王就出了门。他说要去找肉联厂的老李,看能不能买到半只羊。冬日的阳光斜斜地照在街道上,却没有丝毫暖意。
我在店里整理货物,心不在焉。收音机里播放着流行歌曲《常回家看看》,唱得我心里一阵阵发酸。
中午时分,隔壁卖布料的张嫂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进来:"听说你们要回老家?趁着过年前人不多,是该回去看看。我娘去得早,要是能再见一面,我什么都愿意。"
张嫂的话让我更加内疚。娘生前最后一次见我,还是三年前的春节。那时她已经有些病恹恹的,但见到我和老王,还是高兴得像个孩子,非要亲自下厨做一桌好菜。
她站在土灶前,头发已经花白,却依然精神矍铄,一边烧火一边唠叨:"闺女啊,城里生活好不好?吃的用的都不缺吧?你这孩子,咋又瘦了呢?"
那时我只觉得她唠叨,现在想来,那是多么深沉的爱啊。
傍晚时分,老王推着自行车回来,车后座上绑着个麻袋,袋口微微敞开,露出一截白森森的羊骨头。
"半只羊,花了一百八。"老王搓着冻得通红的手说,身上还带着肉联厂的腥味,"明天咱就回去,给你娘上坟,顺便看看你弟他们。"
一百八十元,那时候相当于普通工人半个月的工资。虽然我们的小店生意不错,但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贵了点。"老王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但这钱花得值。家里的老人,活着的时候多孝顺,去了的也得好好祭奠。"
那一刻,我觉得娶了老王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
次日天还没亮,我们就关了店门,拎着包袱坐上了去往老家的长途车。老王把羊肉用油纸包好,装进了一个旧帆布包里。那是他当知青时用的背包,陪伴了他二十多个春秋。
车厢里挤满了人,空气中弥漫着烟味、汗味和各种食物的气味。邻座的大妈从竹篮里掏出两个煮鸡蛋,递给我们一人一个:"看你们起早,肯定没吃饭,吃个蛋垫垫肚子。"
这种人间烟火的温暖,是城里少有的。我道谢接过,蛋壳上还带着余温,剥开后蛋黄喷香,让人想起小时候娘蒸的鸡蛋羹。
一路上,我默默地看着窗外,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窗外的风景从城市的高楼大厦逐渐变成了广阔的田野和零星的村庄。记忆中的小路、池塘、田埂一一在我眼前闪过。
这些年,我以为自己融入了城市生活,其实骨子里还是那个农村姑娘。每当听到熟悉的乡音,闻到泥土的芬芳,心就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
车行至半路,在一个小镇停靠。一个抱着孩子的中年妇女上了车。孩子蜷缩在她怀里,脸色蜡黄,额头上贴着退烧贴。
"师傅,快点开吧,我孩子发烧呢,得赶紧去医院。"妇女焦急地说,声音里带着哭腔。
看着那孩子,我想起了小时候发烧,娘总是熬一碗羊肉汤给我喝。她说羊肉性温,最能驱寒。每次喝完娘亲手熬的羊肉汤,我的病就好得快。
老王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轻声道:"给点羊肉吧,孩子病了,羊肉汤最管用。"
我点点头,从包里取出一大块羊肉递给了那妇女:"煮汤给孩子喝,我娘说这是去火气、退烧的好东西。"
妇女千恩万谢地收下了,眼里含着泪:"真是好心人啊,今年行情不好,肉价贵得很,我们家哪舍得买肉。"
车继续前行,路过一个集市,几个农民工模样的人上了车。他们衣着褴褛,脸上写满了疲惫,却依然高声谈笑着。其中一个看起来年纪最大的,面色蜡黄,不时地咳嗽。
"大哥,您这咳得厉害,是不是感冒了?"老王关心地问。
"没事,干活落下的毛病。"那人摆摆手,却又忍不住咳嗽起来。
老王看了我一眼,我会意地点点头。他从包里又取出一块羊肉:"这个带上,炖汤喝,对咳嗽有好处。"
农民工起初推辞,在老王的坚持下才收下了,感动得眼眶发红:"遇到好心人了,以后有机会我一定报答你们。"
下车时,我发现帆布包轻了许多。一路上,老王见到有困难的人,总忍不住分出一些羊肉。到老家时,原本半只羊只剩下了小半只。
"老王,这样下去,到家就没多少肉了。"我小声说,心里有些着急。
老王却不以为然:"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你娘生前最乐善好施,看见咱们这样,肯定高兴。"
听他这么一说,我反倒释然了。娘确实是个热心肠,村里谁家有困难,她都会拿出家里不多的粮食去帮衬。每年秋收时,她总会留出一小部分给那些家里缺劳力的孤寡老人。

下了车,我们还要走五里山路才能到家。道路泥泞不堪,老王一手提着帆布包,一手拉着我,小心翼翼地走着。
远远地,我看见了熟悉的村口老槐树,树干上刻着无数孩子的名字,其中就有我和弟弟的。小时候,我们总爱在树下乘凉,听娘讲故事。
走进村子,发现变化不小。原本泥泞的主路已经铺上了石子,村委会门前立着一个大喇叭,正播放着什么通知。三三两两的老人坐在墙根下晒太阳,看见我们,都投来好奇的目光。
"那不是王家闺女吗?嫁到城里去的。"一个佝偻着背的老太太指着我说。
"是啊,都多少年没回来了。她娘去世那会儿,她都没回来,听说是在城里忙得脱不开身。"另一个老太太接茬道,语气里带着几分责备。
这话如刀子般刺痛了我的心。娘去世那年,我和老王的店刚开张不久,正是最忙的时候。接到弟弟的电报时,娘已经下葬了。我只记得自己在店里嚎啕大哭,老王手足无措地安慰我,却也无力改变什么。
老家的房子比记忆中更矮小了,院墙上的土块剥落了不少,大门的红漆也斑驳不堪。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院子里杂草丛生,显然很久没人打理了。
"有人吗?"我轻声喊道,声音在空荡荡的院子里回响。
没有回应。
屋内的柜子上积了厚厚的灰尘,墙角的蜘蛛网随风轻轻摇晃。娘生前最爱干净,每天都要把地面扫得一尘不染,现在却是这副模样。
弟弟王建军听说我们来了,匆忙从地里赶回来,脸上的皱纹比实际年龄多了十岁。他穿着打了补丁的棉袄,手上满是冻疮,看见我们,眼圈一下子红了。
"姐,姐夫,你们可算回来了。"弟弟搓着粗糙的手说,"今年收成不好,年年都这样,家里揭不开锅了。"
我这才注意到,弟弟家的锅台上空空如也,米缸里只有薄薄的一层糙米,就连四壁的泥墙上都渗出了湿气,冷得令人心寒。
弟媳李芳端上热水,她是个勤快的女人,虽然环境艰苦,却把能收拾的地方都收拾得干干净净。
我一眼就看出她怀孕了,肚子隆起,但脸色苍白得吓人,嘴唇没有一丝血色。
"啥时候的喜事?"我问,强忍着内心的愧疚。
"五个月了。"弟媳低声说,"医生说我贫血,需要补养,可家里..."她没说完,眼圈就红了。
这个家,就像我记忆中一样贫穷,却比记忆中更加凄凉。娘在世时,再穷也能变出几个可口的饭菜;娘走后,这个家像是失去了灵魂。
老王拍了拍我的手,默默地把剩下的羊肉交给了弟媳:"熬汤喝吧,对身体好。"
弟媳接过肉,眼泪刷地就下来了:"谢谢姐夫,谢谢姐姐。这么贵的东西..."
弟弟在一旁插嘴:"别客气,姐夫一向大方。来,我去地窖里拿几个土豆,咱们晚上炖羊肉吃。"
看着弟弟弓着背出去的身影,我心里一阵阵发酸。记得小时候,弟弟总是有使不完的劲,村里的孩子都不是他的对手。现在却被生活压弯了腰。
傍晚,炉灶上的铁锅咕嘟咕嘟煮着羊肉汤,香气弥漫了整个院子。弟弟家的老黄狗卧在门口,眼巴巴地看着屋内,不时地舔舔嘴唇。
"这狗还是娘在世时养的那条吧?"我问弟弟。
"嗯,都十几岁了,按狗的年龄算,已经是老寿星了。娘走后,它天天趴在娘的床前哀嚎,好几天不吃不喝。"弟弟的声音哽咽了。
我蹲下身,抚摸着老黄狗粗糙的毛发。它无精打采地看着我,眼神中似乎充满了责备:你为什么这么久才回来?
吃过晚饭,我独自去了村后的小山坡。娘的坟前,我摆上了从县城带来的纸钱和水果。
"娘,闺女回来看您了。"我跪在坟前,泪如雨下,"对不起,这些年忙着挣钱,忘了家里还有您,还有弟弟他们。"
风吹过坟头的野草,发出沙沙的响声,像是娘在应答。我在心里默默地问:是您托梦给我的吗?
坟前的土地冰冷坚硬,我双膝跪在上面,感受着骨头与大地的接触,仿佛这样就能离娘更近一些。
记忆中的娘总是忙忙碌碌,从不肯停下来休息。夏天,她顶着烈日在田里插秧;冬天,她披着月光清扫院子。她的手上总是沾着面粉或泥土,但做出的饭菜却总是那么香。
"娘,我带了羊肉来,您最爱吃的。"我哽咽着说,"可惜路上遇到几个困难的人,给了他们一些。您不会怪我吧?"
夜色渐深,冬天的星星格外明亮。我在娘的坟前坐了很久,直到老王来找我。
"回去吧,别着凉了。"他轻声说,把外套披在我身上。
我点点头,却不舍得离开。在离开前,我摸了摸冰冷的墓碑,轻声说:"娘,我一定会常回来看您的。"
回到家里,弟媳正喝着羊肉汤,脸上有了一丝红润。
"姐,这汤真香。"弟媳捧着碗,小口小口地喝着,"感觉身体都暖和了。"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娘为什么会在梦中出现。她是在提醒我,不要忘记了家人,不要忘记了根。
次日一早,我和老王就去了集市,买了米面油盐和一些过冬的棉衣。弟弟再三推辞,我却坚持要他收下:"咱们是亲兄妹,别跟我客气。"
随后,我又去了镇上的邮局,给家里汇了五百块钱,并承诺以后每个月都寄。邮局的工作人员是个熟人,看见我后,意味深长地说:"你弟弟经常来这领钱,但最近半年都没来过了。我还以为你们城里人忙,忘了老家的亲戚呢。"
我低下头,不知如何回应。这些年,我确实因为忙碌而疏忽了家里。每月固定的五十块钱,对于城里人来说不算什么,但对于农村的弟弟一家,却是重要的经济来源。
集市上人头攒动,吆喝声此起彼伏。我买了一张火车票,是去年春运时的硬座,票面上的日期已经模糊不清。我把它夹在了娘的遗像旁边,那是我们全家唯一的一张合影,是弟弟结婚时照的。
"娘,这是回家的车票。我保证,以后每年都会按时回来看您。"我对着遗像说,心中无比坚定。
临走前,我在娘的坟前又跪了一次,保证来年一定带着全家人回来过年。弟弟和弟媳一直送我们到村口,站在老槐树下挥手,直到我们的身影消失在弯道处。
回县城的路上,老王握着我的手说:"以后啊,咱得常回家看看。亲人之间,这种感应,真神奇。"
我点点头,望着窗外闪过的田野和村庄,心中充满了温暖。
梦里的娘不再是那副憔悴的样子,而是如记忆中一样,笑盈盈地站在村口,等着我回家。娘的梦终于不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我每晚都能梦见她笑着对我说:"闺女啊,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
回到县城后,我和老王商量着把店里的一部分利润固定寄回家,帮助弟弟改善生活。我们还计划着来年春节带上丰厚的礼物回乡,给娘上坟,给村里的老人们拜年。
弟媳的孩子出生后,我们又赶回了老家。看着那个红扑扑的小生命,我仿佛看到了新的希望。
我们把县城的房子钥匙留了一把给弟弟:"以后孩子上学了,可以来县城住,我和你姐夫帮忙照顾。"
弟弟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是一个劲地点头。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和老王的小店生意越来越好,但我们再也没有因为忙碌而忘记回家。每逢节假日,我们都会带上礼物回乡,给娘上坟,看望乡亲们。
城与乡,看似远隔千山万水,其实近在咫尺。那根维系着亲情的线,永远不会断。
每当夜深人静,我总会想起那个连续三晚的梦,想起娘瘦骨嶙峋的样子,想起那半只羊带给我们的温暖和感动。
"生在树上的叶,落在地上的根。"老王常这么说,"无论我们走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
风吹过院子里的老槐树,带来远方的思念。从此以后,我的梦中再也没有出现过憔悴的娘亲,只有她站在村口,笑盈盈地等待着我们回家的身影。